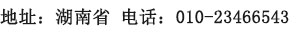自闭症的心理学解析(十三)
第二部
第十三章:意识
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意识?是不是有些运算只能在意识中进行?还是说意识仅仅是我们生理结构中的一种附带现象,一种无用甚至是错觉的特征?
事实上,意识可以进行许多无意识不能做到的特定运算。阈下信息是会迅速消失遗忘的,但是有意识的信息是稳定的—我们想保留这些信息多久都可以。
意识也会将传入的信息进行压缩,精挑细选大量的感觉数据,将它们减少成一组容量很小的符号。这些抽取的信息被接入另一个加工阶段,供我们完成严格控制的一连串运算,就如一台串行计算机一样。
意识的这种传播功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人类而言,语言极大地增强了这一点,它使我们将意识的思考传遍社会网络。
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源于无意识这个观点,许多早期的心理学家都支持该观点,他们认为意识是众所周知的后座司机,永远只能做一名无用的观察者,无法控制周围发生的事情。
被哲学家称为“意识的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意识是有用的。意识知觉将传入大脑的信息转换为一个能以独特方式加工的内部代码。意识有着独特的运算作用,还具有复杂的功能性特征,很有可能就是因此,意识才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被选择保留下来。
我们是否能确定意识的作用?我们不能回放进化史,但能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画面间微小的差别来描绘意识思维的独特性。通过心理学实验,我们能探测到哪些思维过程可以在无意识中进行,而哪些只能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
意识绝不会作为无用的特征被列入黑名单中,有实验表明,意识是非常有用的。
无意识统计,有意识抽样
意识是一种自然分工的过程。在下层,一大群无意识的工人做着累人的数据筛选工作。同时在上层,精选出的董事会理事们仅仅检查情境的一小部分,并缓慢地做出有意识的决定。
无意识思维有诸多能力。从知觉到语言理解、决策、行动、评估和抑制等,每一种认知能力都至少能在阈下条件下进行。在意识之下,存在大量平行运作的无意识处理器,它们不间断地运行,提取关于周围环境的最详细、最完整的解释信息。它们几乎像最优秀的统计学者一样工作,利用每一个最微小的知觉线索、微弱的运动、一个阴影、一个光斑,计算出每一个被察觉到的信息线索,还原到外部世界并解释外部世界。我们的无意识知觉利用传入的感官数据来计算颜色、形状、动物或人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概率。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意识却只窥探了这个概率宇宙的角,也就是统计学家所称的来自无意识分布中的“样本”。意识消除所有的歧义,获得一个最简化的观点,并对当前世界的理解做出最好的总结,之后将这个总结传递至我们的决策系统。
如果一个生物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展,那么它就必须给自己强加一个分工机制,即将意识分成一大群无意识的统计者和一个有意识的决策者。
没有人可以总是只按照概率行动—在某些时刻,需要一个专断的处理来瓦解所有的不确定性并做出决定。任何自发的行为都需要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才能执行。而意识是在大脑中起决策作用的装置——它将所有无意识的可能性转变成一个意识样本,以利于我们进一步决策。
世界带给我们的只有没标好标签的机遇,其结果是不确定的、随机的。无论何时,意识只让我们注意到关于这个世界成千上万种解释中的一个,以此来解决问题。
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跟随着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的脚步,发展他的观点,他首次意识到即使是最简单的意识观察,都要以复杂且杂乱无章的无意识概率推断为源头,他的观点如下:在这个可爱的春天的早上,我望向窗外,看见了一朵盛开的杜鹃花。不,不!我没有看到它,那只不过是我描述所见之物的唯一方式。那是一个命题,一个句子,一个事实,但是我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命题,也不是一个句子,更不是一个事实,而只是一个画面,某种程度上我通过陈述这个事实让自己能够理解这幅画。这种陈述是抽象的,但我所看见的却是具体的。虽然只是用一句话表达我所看到的东西,但是我也需要进行一次归纳推理。事实上,我们的知识如同一块由纯粹假设编织起来的毛毯,不断地被归纳、证实和改善。如果不在每一步都进行一次归纳,除了茫然注视外,知识上不会有任何长进。
在贝叶斯首次探索数学领域之后,现代认知科学家所称的“贝叶斯推理”又被皮尔斯称为“溯因推理”。贝叶斯推理使用一种倒推的统计推理方式,推断出隐藏在观察结果背后的原因。在经典概率论中,我们通常只知道发生了什么,例如“某人从一副52张的牌中抽了3张”,这种描述使我们能够对特定的结果赋予概率值,例如“3张牌都是A的概率是多少”。然而,贝叶斯推理让我们从相反的方向进行推论,从已知的结果到未知的来源。例如“如果某人从一副52张的牌中抽了3张A,那么这副牌被做了手脚,包含4张以上A的概率有多大?”这就是所谓的“反向推理”或“贝叶斯统计”。把大脑当作一名贝叶斯统计者是当代神经科学中最热门而且最富有争议的假说之一。
我们的脑一定是在以一种反向推理的方式运行,因为我们所有的感觉都是模糊的,许多不相关的事物都能引起类似的感觉。例如,当我把玩一个圆盘时,虽然实际上投射到我视网膜上的是一个扭曲的椭圆,但它的边缘却呈现出一个完美的圆,而且关于它的解释,还可以兼有其他许多种版本。只要是土豆形状的物体,不管在空间中处于什么方位,总能在我们视网膜上投射出相同的形状。如果我看到的是一个圆,那只是因为我的视觉思维无意识地思考了这种感觉输入的无限多种可能,最后选择了其中的“圆”作为最可能的解释。因此,即使我知觉到盘子是一个圆,即使这似乎是一瞬间的事,但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推理过程,这个过程排除了关于这个特定感觉的数量惊的其他解释。
神经科学提供了许多证据,证明在中级视觉阶段的大脑考虑了大量关于感觉输入信息的其他解释。例如,单个神经元可能只知觉到椭圆的整个轮廓的一小段。这个信息可以与各种形状和运动模式兼容。然而,一旦视觉神经元开始互相沟通,将它们的“票”投给最佳的知觉对象,就能使全部神经元达成共识,确定其形状是否为椭圆。夏洛克·福尔摩斯曾说过一句话:当你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情况,无论得出的结论多么令人难以置信,那也一定是真相。
严谨的逻辑统治着大脑的无意识回路--这些组织良好的回路能够对我们感官输入的信息进行统计层面的精确推理。例如,在中部颞叶运动区域MT区,神经元通过一个狭窄的观察孔,即“感受野”来觉察物体的运动。在这种尺度下,任何动作都是模糊不清的。正如你通过一个观察孔看根棍子,并不能准确地判断其运动方式,它可能垂直于自身进行运动或者沿无数的其他方向运动。这种基本的不确定性被称为“孔径问题”。在无意识的情况下,MT区的单个神经元会遭遇孔径问题,但是在意识水平上却不会,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也并不会知觉到模棱两可的东西。因为脑会让我们做出决定,并做出它所认为的最有可能的解释,即基于最小运动量的原理推断出棍子看起来总是以垂直于自身的方向运动。一大群无意识的神经元评估所有的可能性,但是意识只接受一个精简的报告结果。
意识通过解决“孔径问当我们观察一个更复杂的运动形状时,如一个运动的矩形,虽然局部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已经有办法解决。因为矩形的不同边提供了不同的运动线索,所以把它们整合起来就知觉到了一个唯一的运动方向。只有一个方向的运动能满足矩形的每一条边产生的限制条件。我们的视觉脑对此进行推理,使我们能够看见唯一严格符合条件的运动。在记录神经元时,研究者发现这种推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整整0.1秒,另外,在MT区的神经元仅能“看到”局部运动,它们改变思维方式直到对整体方向编码完成,还需要花费-毫秒的时间。然而,意识对这种复杂的思考过程无所知。主观上,我们只看到最终的结果,即一个平滑运动的矩形,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最初的感觉是不确定的,也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神经元回路必须通过努力工作才能理解这些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