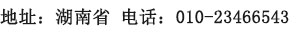政治与友谊:
德里达访谈录(上)*
苏仲乐译
译者按
年4月间,雅克·德里达教授访问加利福尼亚大学厄湾分校,借此机会米歇尔·斯皮瑞克(MichaelSprinker)对其进行了一次访谈,下文便是此次访谈的记录?在访谈之前,先以书面形式给德里达教授提出了几个问题,以便给讨论提供一个大致的范围?但是,像此类访谈常有的情况一样,实际所谈还是牵扯到那些书面问题并未涉及的几个方面?这篇访谈录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谈话的原貌(德里达基本上是以法语作答,而斯皮瑞克基本上讲的是英语),并由塞西尔·芮福林(CécileRivoallan)整理成文?整个谈话是围绕着所谓“阿尔都塞主义”和“解构”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来进行的?
△图为雅克·德里达。
米歇尔·斯皮瑞克(以下简称“米”):20世纪60年代初,您应伊玻利特(Hyppolite)和阿尔都塞之邀执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我想您肯定知道阿尔都塞本人以及有关他的一些情况,或许对他早在50年代的一些作品也是有所了解的?但是,那次回去执教应该算作第一次正式的机会,使你们之间有了正式的交往,并近距离地了解他所从事的工作等情况吧?那么,您不妨谈谈在此期间的情况,谈谈您与阿尔都塞以及他的学生之间的关系,甚至您自己的工作与阿尔都塞的研究之间的联系?
雅克·德里达(以下简称“德”):实际上,我们之间的交往——甚至包括一些哲学问题很早就开始了?我是年到年就读于巴黎高师的?年秋,我刚到学校便与他相识了,而在此前,对他可以说是闻所未闻?我与他第一次碰面是在他的办公室?当时他在这个学校已经执教数年?用当时高师学生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辅导教师”(ca?man),意即哲学研究方面的指导者?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才知道,原来我俩都出生于阿尔及尔,相差12岁:他是年生人,而我则生于年?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当时就聊起了一些陈年往事,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而已?说起来也挺矛盾的,他的课我连一门都没听过?一方面,他在三年级学生(也就是那些准备参加“教师资格认证”的学生)的教学上投入的时间本来就少得可怜;另一方面,那时的他已经是疾病缠身(我当时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病症,有人说是他从战俘营出来后患上了肾功能紊乱)?他根本就没教多少课?因此,我在高师的这段时间里,与他虽然关系甚为密切,但根本不涉及学习上的事情?除此之外(我现在也在努力地回想当时哲学上的一些事情),当我给他写“教师资格认证”论文的时候,在此前一年我已经……
米:您那篇论文是关于什么内容的?您还记得吗?
德:记得,那是年?
米:不,我的意思是说那篇论文的题目您还记得吗?如果想不起来就算了?我也只是出于好奇,随便问问而已?
德:当时我对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已经思考了一年时间?这是为“高等研究文凭”(Diplomed’étudessupérieures)所做的准备?我认为,我这篇关于时间的论文已经有相当的难度,而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成了这篇论文的特点?阿尔都塞跟我说:“我无法评判这文章?对于‘教师资格考试’而言,它太复杂?太晦涩了,也可能有一定的危险?但是鉴于我无法衡量它,我将征询福柯的意见?”米歇尔·福柯当时还只是里尔大学的助理教授?他也来高师授课,我也听了他所讲的一部分课程?我和福柯的关系也不错?他读过我所写的关于胡塞尔的一些东西,也比较赞赏?读了这篇论文后,这次他告诉我:“我看,它要么是‘特优’(A+),要么就是‘不及格’(F)?”我之所以提起这段趣事,是因为他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我与学术权威的关系,而“教师资格认证”考试委员会就是学术权威的一个典型代表(那一年我也最终未能通过这次考试),同时也因为就在这篇论文当中,关于胡塞尔的研究文字我写了页?在那个年代的特定的学术圈里(甚至不乏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有人对胡塞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说的是一种特殊的兴趣,它不同于萨特和梅洛庞蒂对胡塞尔的理解?而巴黎高师和“教师资格认证”考试委员会的成员们对胡塞尔仍然所知甚少?难以接受?
米:是的?50年代还是如此?
德:我倒是想起了陈德草(Tran-DucThao)的那本著作——《现象学与辩证唯物主义》(PhenomenologyandDialecticalMaterialism)?这位高师学长和阿尔都塞同年毕业,后来回到了越南,他曾经以具有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对现象学进行研究,而且在得到大家的激赏之后(我记得福柯在课堂上,也可能是在私下交谈中就曾夸奖过他),他就发生现象学(geneticphenomenology)的一些问题(被动发生?时间性)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再阐释?大概是这本书对我影响颇深,在我关于胡塞尔的论文当中应当可以看到它的印记?
陈德草虽然对胡塞尔多有批评,但是围绕着现象学的发生这一主题,他借助于发生心理学和皮亚杰(Piaget)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转化为,或者如有些人所说,转码(transcode)为一门有关心理发生学?本体发生学以及系统发生学发展的科学(ascienceofpsychogenetic,ontogenetic,andphylogeneticdevelopment)?我现在已经无法确切地想起那本书的细节,但是在当时这本书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一方向会在某些确定的哲学环境中产生,它利用胡塞尔的超越性问题,完全以一种质料的(non-formal)?非观念论(non-idealist)的方式(也就是以康德的方式),来质疑科学性?质疑理论实践以及认知态度的出现?质疑科学客观性何以可能,与此同时超越了经验主义,至少是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或者实证主义,也超越了仅仅作为“知觉现象学”的现象学?那些马克思主义(而且首先是阿尔都塞——这种情况始终如此)在哲学和政治上的敌人?那最难对付的敌人就是《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一书的作者梅洛-庞蒂?不仅如此,梅洛-庞蒂战前也曾任巴黎高师的“辅导教师”,应该在这所奇特学府以及它所容纳的?同样奇特的“团体”的奇特的历史当中为所有这些重新定位——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尤里姆街的哲学家谱系中为其重新定位?现在还有一项工作尚待完成,那就是对这个国家过去数十年间丰富的生活和知识风尚进行梳理?
那时候我与阿尔都塞的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是感情深厚(这种友谊一直得以保持,甚至后来虽经历冲击也不例外)?但是我俩之间哲学方面的交流若不能说完全没有,那也是少之又少?不管怎么说,这些交流完全是内在的(正如它们确实一直持续着一样)?(还是与你刚才的话头接续起来)然后,我就离开了高师?在获得“教师资格认证”后,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待了一年(—)?然后就是服兵役(身份是教师,而且穿的是便装)?年我又回到了巴黎?在索邦大学做助教的那四年间,我与阿尔都塞也数度碰面?我记得自己年曾经将《胡塞尔几何起源引论》(“IntroductiontotheOriginofGeometrybyHusserl”)的手稿交给了他?这本书年面世?关于这个题目,阿尔都塞写给我一些非常丰富和鼓舞人心的东西?在此前一两年,他已经出版了关于孟德斯鸠的第一部著作?关于那本书,我们还有过信件往来?他那时经常生病,时常不在高师?但我还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在影响着他?年到年,他被邀请去高师授课?
在我自己作为“辅导教师”去高师任职之前(这一来是有阿尔都塞之邀,二来因为伊玻利特的举荐,当时伊玻利特已经离开高师去法兰西学院CollègedeFrance任职了),我偶尔会替他临时补缺?我在那里有一间办公室,可以处理“教师资格认证”的事情?我当时已经得到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认可,我之所以谢绝就是为了能够在巴黎高师获得一席之地?于是,年我就去了高师,这一待就是二十年的光阴?我也因此而有幸与阿尔都塞共事二十年?能持续地与大家共事这么长的时间,现在看来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最起码是在法国的同一所学校里共事这么长的时间——希利斯·米勒倒是与我共事二十二年了,但却是在三个不同的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以及加大厄湾分校)?在那之前的年,我已经在高师讲授有关胡塞尔的课程了?
米:就是给埃斯塔布莱?朗西埃?巴里巴尔参与了《读资本论》写作那拨学生讲吗?
德:不是,不是?这里面就没有埃斯塔布莱?但是却有巴里巴尔?马舍雷(Macherey)那时候已经离开了高师?巴丢也离开了?他们都比巴里巴尔稍长几岁?但是我见到巴里巴尔和朗西埃时,他们已经获得了“教师资格认证”,与此同时我还认识了其他一些人,恐怕你不大会知道吧,像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Miller),他年龄要小一些,米歇尔·托尔(MichelTort)?帕特里克·居约玛尔(PatrickGuyomard)?克劳德·拉邦(ClaudeRabant)以及伯纳德·波特拉(BernardPautrat),还有其他很多人?但是,那时很快就——我现在也尽量挑一些你们感兴趣的事情说——很快到了年和年间,就在我开始授课的那个时期,时间到了那个重要的节点上:拉康此时也应阿尔都塞的邀请来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这个邀请是由阿尔都塞还有正在参加拉康研讨班的一些学生发出的),而阿尔都塞也开办了一个研讨班,也就是因为这个研讨班才有了《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而这一段时期他也恰好身体康健?积极活跃?
米:对不起,我插一句?你们早在50年代就已经对心理分析和弗洛伊德主义产生了兴趣吗?你们是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组合,还是此时才致力于心理分析的研究?
德:在那之前我几乎没怎么读过拉康的什么著作?或许读过《文字的审级》(TheInstanceoftheLetter)[1],但是我记不起来到底是什么时候读的?
米:那时候他就没有什么著作可以读呀!或者说是少得可怜?《文集》(Ecrits)也不过是在年才出版的?
德:没错,但一些广为人知的文章那时已经发表了,如《罗马讲演》(“TheRomeDiscourse”)和《文字的审级》?
米:这些文章在当时广为人知并广受赞扬吗?
德:广受赞扬?……起码在这些圈子里是广为人知?我当时也只是读过《文字的审级》,或许还有《罗马讲演》,但基本上是走马观花?如果你想了解的话,我不妨说说?我所处的那个环境挺奇特的?我基本上一直在从事胡塞尔的研究工作?但那一年我教的课程却是“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历史”,这门课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学生在听?我与巴里巴尔?朗西埃以及在我指导下参加上一年“教师资格认证”的学生关系密切?那一年说也荒唐,在我以“辅导教师”身份开始讲课时,阿尔都塞主持的那个研讨班开始了,这下吸引了那些学生所有的注意力?我觉得很不自在,你知道就是感到突然就被晾到一边了?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两次阿尔都塞的研讨班,比如有一次是朗西埃作报告?后来这些报告中的一部分发表了?
然而,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自己的处境似乎比较尴尬?马克思主义领域之内的整个难题性对我而言毫无疑问是必要的?这个领域也是一个政治的领域,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与党的关系,而我又不是党员?此时的法共正在逐渐告别斯大林主义(而在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它以独裁的方式高高在上)?但是,与此同时我又发现这问题性——应该说是幼稚的,或者说是缺少文化,甚至更甚——它对于批评的?超越的以及本体论的问题过于麻木,而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却是必要的——甚至必须反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但无论如何要经过他们?
米:我们本可以把下面这个问题放在后面反复探讨,但是我们还是现在就不妨谈谈吧?在那个理论领域,或者干脆就说在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们探索的那个领域之内,您觉得最具难题性的有哪些方面?
德:如果对其做一个迅速的回顾,在我看来很多问题好像是被忽略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历史性问题,或者说历史的概念问题?我当时也卷入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论争(关于观念的客观性历史何以可能的条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语言和科学的历史性何以可能的条件,还有胡塞尔式的唯心论以及超越目的论的必要性和局限,历史性和客观性之关系等问题)?我们不妨说,关于历史的历史性的主体?客体的客观性的主体,不是从非历史的观点出发,而是提出另一类型的质疑(我相信这类质疑是基础性的,因而也更彻底?更具批判性?更具“解构性”,也就是说,甚至对批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判来说都是“批判的”)?我觉得他们应该通过这种类型的质疑来检验他们关于历史的观念?长期以来我并不是想唱反调,我只是想说:“你们必须慢一些?客体是什么?科学的客体又是什么?”在我看来,他们的话语似乎屈服于某种理论主义或者新奇的科学主义,而这是我应该提出挑战的?但是,我却没有任何动作,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的问题只不过是粗鄙而自私的批评,是与右派或者左派,特别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即便我不是党员,但我对那种状况却是了解的?我知道,举例来说,这种理论主义或者科学主义的指控完全可以从法共的观点出发提出来,而且还是以一种非常概略的形式提出,或者至少是以党的语言提出来的,对此我实在难以认同?
因此,面对这个几近于理论主义,也与首字母T大写的理论(theory)在本质上不无相似的东西,关于这套理论?这门科学,大写字母的使用也未免过于武断和夸张,面对这些现象我没有反应,保持着沉默?所有那一切对我来说似乎都是让人忧虑?存在疑问且不无危机之虞,但我这都是从一个并非人文主义或者经验主义的视角来看的?阿尔都塞正在指挥着与一个确定的霸权所进行的斗争,而这一霸权就是党内可怖的教条主义和哲学的僵化——在我看来,这场斗争(由于当时情况的局限)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不愿也不能在这时候阐明这些与来自党内的问题虽然距离很远?但却相似的问题,而阿尔都塞正在与党内的这些问题进行斗争?即使我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我也不能说:“没错,它是理论主义而且会因此而导致政治上的麻木?”我就这样通过有些折磨人的缄默而将自己与外界隔开了?此外,我现在所描述的这一切很自然地就与别的一些人所说的一种如果不是个人的,最起码也是知识的恐怖主义联系在了一起?我与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还有其他一些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还是可以说,存在着一种理论上的胁迫:如果你通过一种我们所说的像是现象学?超越的或者是本体论的风格来阐述问题,就会立即被认为是可疑的?倒退的?唯心甚至是反动的?而且由于我已经在用这些方式阐述问题,那么这种表面的现象被复杂化到了极致,到了它所针对的人竟也无法卒读的地步?毫无疑问,我并不认为这些阐述是反动的,但那种胁迫却是存在的?最起码,对于当时正在从拉康主义当中所感悟到的东西,我也有同样多的实际问题?
米:对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一些您所感兴趣的任务,他们的态度让您感到了一种胁迫?
德:是胁迫,但是我也在心里进行反抗?
米:的确如此,但与此同时,您又认为重要的是,阿尔都塞及其学生们探讨历史?科学?客观性等问题的方式需要与这个难题性联系起来?但是在这一点上您并没有就这些问题与他们进行直接论辩?
德:那个社会空间不允许我这样做?
米:因为您同时也感到,从党内来看,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是非常有希望的,您也就因此而保持了沉默?
德:对,正是如此!我也因此感到有点孤立,同时我又感觉到我所研究的这个难题性从长远来看更有必要性?更加不可避免?尽管如此,我与此同时也觉得我发现了一个更加难以表述的问题:既可以说是公开,又可以说是秘密地借自——当然不是我了——对我非常重要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尽管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有否定?有公开的反对,但无论如何,存在着一种得自于他们的阅读模式和问题类型的结合(我认为这种结合过于草率而且对其定义不够明确)?比如像下面这些问题:在哪些条件下客体的客观性才是可能的?为了使它们通过一种形式的或者超越的逻辑,抑或基本的本体而服从于一般理论(generaltheory),(知识或者理论的)客观性区域(regionsofobjectivity)如何能够层级化?在那种同时也是一种认识论主义(epistemologism)(唉,这也是与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当中占统治地位的教条的经验主义决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理论主义当中,它的确是一个客观性区域的问题?是各种区域性本体论的一个问题,这些作为客观性理论的区域性本体论关于作为客体的实体的限定(determination)?关于历史以及这种限定暗含的意义没有任何(比如,海德格尔式的)问题?这不愿把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搞清楚的躲避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恼火,特别是阿尔都塞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素来心向神往,但他从未有过任何公开的表露?
米:在他发表的任何作品当中,我想不起来他曾经提到过这些人的名字?
德:如果我可以说得唐突一些,在阿尔都塞看来,海德格尔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且无法绕过的思想家?既是强劲的对手又是真正的盟友或者说是实际上的援手(阅读阿尔都塞的所有作品都应循此线索)?就像我刚才跟你所讲,我们在一起时很少谈论哲学,即便谈论也是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或者揶揄讽刺,有时平和有时并不那么平和?大多时候总是有一个潜在的背景,也可能是在一些严重误解的情况下谈论的?然而,医院的最后那些年,曾多次对我说:“我给你说呀,你可得跟我谈谈海德格尔?你一定得给我教教海德格尔?”他也读了一些海德格尔的著作?可他读一读就又放下了?
米:您怎么知道在阿尔都塞看来,海德格尔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他并没有读过多少海德格尔的作品,海德格尔能对阿尔都塞的思考产生什么影响呢?
德:我们都在以自己特有或习惯的方式工作?阅读?不读?不读而有所读,读而无所读,在不回避中有所回避?有所否认?阿尔都塞亦复如此?而且,反过来说,任何时候都要记着,研读和阐释阿尔都塞都离不开那个非同寻常的“经济”?但是,我可以确证的是,阿尔都塞(言谈中)经常提及海德格尔,而且他一直都不曾像某些人那样毁誉或者贬低海德格尔的思想,哪怕是出于你所知道的政治原因?但是,你很清楚,在马克思主义和海德格尔主义之间存在的一种确定的配置(configuration),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吸引—拒斥关系乃是本世纪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如果说我们已经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严肃的思考,那么这种思考还远未完成?
米:那么这是由于萨特的影响还是由于伊玻利特的影响呢?
德:阿尔都塞或许应该说,这一轨迹毫无疑问更为复杂?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是海德格尔的身影不仅仅存在于阿尔都塞的研究当中,也存在于那一时期所出版的所有著作里,那就是《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我曾经在《心灵》(Psyché)(Désistance)一文中的一条注释里说,在这个世纪四分之一的阶段当中,一些法国学者的著作当中没有一部明确地提到海德格尔,但后来这些人(比如,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都不得不私下或公开地承认,海德格尔在他们的思想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另一种法国知识史的另一种路数?
米:在您手头上既无现成文本,而最近又没有阅读阿尔都塞著作的情况下,我知道这的确是强您所难,但我还是想让您尽量想一想在什么地方可以发现这种踪迹?请您说说在阿尔都塞文本的哪些地方可以找到呢?
德:那就让我们以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这个大问题来说吧?在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LetteronHumanism)就抨击或者说是“解构了”作为形而上学的特殊的人道主义?阿尔都塞在其所有关于反人道主义的文章当中,从来没有引述过海德格尔?然而,他的确论说人道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或者说,形而上学是人道主义的,这一说法恰恰与海德格尔的那一环节形成了呼应(在《人的结局》(TheEndsofMan)中,我试图通过法国的“人”将那一时期的情形以某种形式体现出来)?在那篇文章当中,海德格尔论述道,马克思是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形而上学者,而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中,他的确说过,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的概念是对存在的一个了不起的阐释?在对马克思表示敬意的同时,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明确表示,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或者说他的唯物主义并非物质的哲学,而是劳动的哲学?从根本上而言,他并不是关于作为物质的存在的思想家,而是关于作为劳动的存在的思想家?要阐释马克思必须从劳动和生产的视角切入,而不是从物质质料(materialsubstance)入手?二十年之后,你很难想象说,阿尔都塞(也包括福柯)当时那些所有反人道主义的著述和这个文本毫无关系?《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可能是当时法国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也是至今还被中科携手共抗白癜风白癜风怎么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