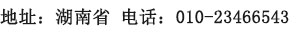bouttheproser
本期
一清风宛频李方蕾潘莉红
(以上排序不分先后)
本期组稿::李东配画:宛频李
一清风苋菜和苋菜汤
我喜欢吃苋菜,尤其喜欢苋菜汤泡饭。那红红的,暖暖的苋菜汤让人垂涎。小时候我身体十分瘦弱,用现在的话叫营养不良。一双大眼睛镶在亮亮的脑壳上,显得格外醒目。三年生活困难时期。我甚至连饭都吃不饱。人更廋了。用同学们的话说:三根筋挑着一个头。一次我饿得都上不动学了。妈妈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就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米煮了。也不知道她从哪儿又摘了一把苋菜炒了炒,加入一碗多水,把那一小碗米饭倒入,然后又拿起家里盛面的空铁桶,倒过来,用手轻轻地拍打,只见有少许面粉从里面飘落下来。她用勺子搅拌下,又添把火熬了熬,背着弟弟妹妹,端到我面前,叫我到灶台后趁热吃了。我先把红红的米饭和菜吃得一干二净,然后把碗底仅剩的一点红汤也喝了个碗底朝天。妈妈看了,拿过碗,又把锅里剩下的一点苋菜汤盛了,叫我都喝了。我推开碗说:妈妈,你喝吧!妈妈说:孩子,你喝吧!喝了补血。记得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菜饭。也是第一次听说苋菜汤能补血。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连“补血”的苋菜汤也越来越难喝到了。妈妈就带我去挑野苋菜。说实话,野苋菜味道也不错,可就是炒出来后,没有红红的苋菜汤。我怀念红红的苋菜汤。而且相信它能补血。后来,生活慢慢变好了,我也长高,增重了。但心里还一直怀念那红红的苋菜汤。
再后来,我独立成家了,但只要季节相当,苋菜,总是我家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但吃着,吃着,总感到没有以前苋菜的味道了。汤也觉得没以前的红了。再后来我退休了,竟然萌发了要自己种苋菜的念头。说干就干,从市场上买来了苋菜种子,按照网上的指点。准备种苋菜。可是漂亮的小区岂能让人随便种菜!我不得不偃旗息鼓。看来,儿时的苋菜只能种在心里了。
母亲节那天,我回家去看望年届九旬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在菜场转了一圈,买了些荤腥鱼肉和新鲜蘑菇。准备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就在转身离开时,忽然发现在菜摊的边上,有一大姐面前有一篮子的苋菜。斑驳的阳光洒在苋菜上。显得那么鲜嫩。我弯腰抓起一把,看了看,又闻了闻。一股清香。大姐说:自家种的,未打农药。一顿吃不了,放着,明天就蔫了,不好吃了。我点点头。买了一大把。
未到父母亲家里。老远就看见妈妈在门口张望。我知道她在等我。我搀扶着妈妈进去。爸爸接过塑料袋说:你买那么多菜干吗?我笑道:不多,那鼓鼓囊囊的大包是苋菜!妈妈说它补血!妈妈笑了,说:儿啊!你还记得苋菜补血?我点点头。她继续道:唉!那是你小时候没得吃,人又廋,妈哄你的。只听说过猪肝补血。苋菜能补什么血噢!我懵了。望着妈妈慈祥的脸庞。我相信她是认真的。回来后,我上网查了查:“科普中国”百科科学词条写道:苋菜,茎叶可食用;根、果实能入药。
苋菜亦能补气、清热、明目、利大小肠,且对牙齿和骨骼的生长可起到促进作用,并能维持正常的心肌活动,防止肌肉痉挛。还具有促进凝血、增加血红蛋白含量并提高携氧能力、促进造血等功能。还可以减肥清身,促进排毒,防止便秘。哇!苋菜一身是宝啊!
看来,这回妈妈没说对。苋菜真的也有促进造血的功能。第二天,我又去了菜场,转了一圈也没看到苋菜。我想,苋菜能不能补血已不需要去深究了。重要的是:妈妈那一颗给儿子补血的心!我要常回去看看她老人家。
宛频李
穿行
是的,穿行让人类在真实的世界里虚拟一切。
一切的发生都显得那么突然,一切的突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如露如电如泡影。白驹过隙的生活里,不知不觉冬去春来四季轮回,记忆穿行,在和哥哥的告别声中,在汉字书写中,在和妹妹分享钙片糖豆的快乐中,在姐姐的婚礼上,我们很快一个个长大。左眼欢笑右眼悲伤,随着侄女外甥下一代人的诞生,母亲终于在61岁时患胃病病逝,院子里的泡桐树开出所有的花朵又落下所有的花朵,一切的喧嚣归于寂静,一切的寂静终在最后归于尘土的虚无。是的,只有那庭院里的大地,那虚无而又坚实的大地,土褐色的黑黝黝的大地才是抚慰,才是落花与生命的归属地,才是世间所有有关穿行虚拟甚至穿越遐想的真实归属。
七岁的我和三岁的妹妹如今早已步入中年,但我们仍清晰记得童年岁月,记得母亲穿白大褂来回穿梭,为病人打针问诊的情形,记得她教育我们的情形,记得她不辞劳苦下班回来就匆匆进入厨房为我们做菜烧饭的情形,我们童年正处七十年代,虽然父母都有工资,但因姊姊多,家中经济并不宽裕,但勤劳的母亲总能想法刨些野菜腌制点咸货改善我们的生活,那些被叫做“扫帚苗子婆婆丁”的野菜带着湿泥巴,夹杂着枯叶,层层叠叠,卷卷地散落在厨房地下,母亲总是一把把甩去泥巴,一根一根摘下枯叶,不厌其烦用水洗了一遍又一遍。我记得当初那些带着泥巴气息的野菜,它们被母亲拌上面,撒上葱花浇上油做成圆圆的饼,蒸出锅,拌上咸蒜泥,还要盛在盘子里均分在五个碗里……,母亲是位魔术师,她不停地舞动着,让它们发挥各自的使命和价值,直到那堆卷卷的野菜变成可口的蒸饼,稳稳地真实地童话般出现在我和姊姊们面前,出现在我们家吃饭的方桌上。还有那些咸货,萝卜干芥菜……,母亲洗干净它们,起初弯着腰在院子里翻晒,后来又选择一个午阳高照中午,把它们一个个小心的放入褐色的坛子里,撒上盐封存。母亲腌制的咸菜,不仅色泽看起来总是与别人不同,显得那样鲜润,而且味道也比别人腌得脆一些,逢到左邻右居来我家串门,母亲总是慷慨的把存放的并不多的咸菜主动送给她(他)们……
有一次,咸菜被母亲送完了,我们姊姊在吃饭的时候开始抱怨母亲。母亲淡淡笑了笑,说等下次再腌。送走的咸菜一次又一次验证着邻里友情与母亲辛苦劳力的交换。但有时候,邻里友情和劳力很难实现对等关系!这一点,母亲当初被叫做“珍妹子”(母亲的小名)的时候,就已经在老家那群可敬的乡亲中间知道答案!
是的,什么能代替那些朴素岁月里的亲情?友情?什么能替代母亲对那些卷卷的野菜,对那些晾晒的萝卜芥菜所寄予的情感?什么能替代她对于我们,对于左右邻居的真情和亲情呢?!
没有什么能替代亲人的深情和亲情,永远不能!当时光虚拟,16岁的母亲当初带着哥嫂的白眼,带着乡亲们凑来的学费,带着勇气,离开家乡凭勤奋之力拓开卫校大门的时候,她就明白了人间友情的价值!
年清明节回家上坟,我在老家柜子里无意翻出了一张母亲搂着我和妹妹的老照片。发黄的照片上,妹妹歪着头坐在母亲的怀里开心的笑着,而我也只有七八岁光景,乖巧的依偎在母亲身边,我们小时候母亲可真年青啊,笑起来时,嘴角还有两个浅浅的梨涡。是的,老家的那组柜子据说是乡下的大姨和大姨父送的。是送给年青的母亲和父亲的结婚礼物,记忆中,当大姨父吸着卷纸烟站在老家庭院里和父亲有一句无一句的搭讪的时候,母亲和大姨在厨房里快乐地忙活着,他永远不知道五百元人民币的秘密(母亲背着大姨夫偷偷硬塞给了大姨元),他骄傲地作为一位近亲慷慨地送出了自己的礼物和作品,一名木匠的心血之作。他带着有一门城里亲戚的骄傲,带着一名男性木匠工的陶醉,自豪地在酒桌上接受着父亲敬酒,惬意地从干涩的嘴唇间吐出一串又一串的烟泡。在他微酣的醉态里,我蓦然想起自己作为一名2岁到7岁的幼儿在乡村的成长历程,想起大姨父把白面馍省下给我吃的情形。在经济拮据的农村,大姨平日省吃俭用刻意“扣下”的二个白面馍馍,一个给我,一个给大姨父,给我们增加营养,但大姨父的总是把自己仅有的那个白面馍也递给我,然后和大姨一起吃黑面馍。大姨父瘦,粗糙的黑面馍总使得他鼓起腮帮,费劲地咀嚼,而且总有些馍渣会顺着他深深的法令纹掉下来,挂在他胡子拉碴的嘴角。
时光荏苒,随着家里经济与物质上的改善,现在的我们天天都吃白面馍。我和妹妹偶尔在单位体检中查出有心脏病早搏的病症,被医生告诫要尽量多吃点粗粮,是的,多吃些粗糙的杂粮馍黑面馍,有益于城市人的健康。什么时候,城市里的我们在饮食上归回了?!
是的,归回了以前的时代,那些缓慢的,卷卷的清薄的木屑不停掉落在浅褐色泥巴地上的静默时代?静默的时代,木屑不讲话柜子不讲话白面馍馍不讲话,庄稼不讲话村庄不讲话大姨大姨父不讲话,它(他)们各自固守着一种姿势,顽强地在时光里缄默地等待,是的,它们在等待,等待穿行过那长长的岁月,穿越生活中最准确的位置,演绎着历史,演绎着长辈们内心的深情。是的,我看到庄稼看到乡村看到刨子(木匠的一种工具))看到木屑,看到画着百合花的土黄色马粪纸封面的字帖(幼时母亲用手工做的给我和妹妹临摹用的字帖),看到大姨父掉着馍渣的胡子拉碴的嘴角,看到母亲年青时的微笑,看到厨房里的咸菜罐子,也看到那组矮矮胖胖敦实的柜子……是的,柜子很矮但柜子坚固,不像人的身体会患病会衰老,柜子当初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父亲说大姨父选的是杨树木,杨树木做出来的柜子挺板不容易变形,可大姨和大姨父后来在岁月里陆续变形,我上大学的时候,听母亲说先是大姨害咳嗽病,不仅喘得厉害,腰也渐渐佝偻起来。大姨父不分昼夜的照顾着,直到大姨来到县城住院后,大姨父的腰竟也弯了下去,成了虾米一样的形状。大姨住了一周院,咳嗽病终于好了。但大姨父却病了,并且病得也住了院。患了肺痨的大姨医院,半年后,亲爱的大姨旧病复发也随之而去。也就在那一年,我的唯一的哥哥也遭遇了车祸英年早逝。三年后,母亲终于也撒手人寰。
是的,母亲涅槃那天,一切显得那么安静,在“阿弥陀佛”的佛号声中,她静静看了看我们,是的,没有表情,她只是静静看了看我们姊妹四人,看了看围在她周围诵佛号的佛友,又看了看熟悉的家,她的眼光似乎在寻找,父亲和一位亲友去布置墓地的事情还没回来,还没有回到家里,母亲是在寻找父亲吗?一位和她相濡以沫相伴了一生的爱人,还是在找晓雯?晓雯是母亲的孙女,哥哥唯一的骨肉。晓雯在她父亲车祸去世后就被改嫁的母亲带走了,生活在澳洲,母亲如何能着急地呼唤到她的归来?!
是谁说过,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改嫁(改嫁到国外)的嫂子有再次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她却永远没想到,是她的无意造成了老母亲不能和孙女相亲相爱,相互偎依的残忍事实!爱的悲惨,莫过于失去;悲惨的爱,莫过于缺失。缺失让我拔不出悲哀的情绪,缺失让亲情惨淡了颜色,缺失让爱毫无光泽。缺失让人在茫茫大海找不到港湾。
悲伤是生命中疼痛的海洋,漫溯的潮水愈渐在岁月里渐渐的退去,隐约中,我的耳边又想起泰戈尔先生《人在旅途》的一段话,“我坐在络绎不绝的旅人的哀泣和欢声的旁边,注望着,沉思着,深爱着。我对他们说:‘祝你们一路平安,我把我的爱作为川资赠给你们。因为行路不为别的,是出于爱的需要。愿大家彼此奉献真爱,旅人们在旅途互相帮助。”蓦然,我又看到了那支用来书写的笔。什么时候,现实离间了虚拟和无数假设,远远地推开了我们,隔离出无法逾越的生与死的界限?在那道界限之外,是什么让我们匿在生活的平淡与无奈里,变得越来越麻木不仁起来?冷漠是风霜,一层层随着奔跑的岁月渡上额头,把我和妹妹由儿童催到少年和青年,又由青年催成了中年,现在,越过岁月的年轮,经济的富裕与时间的松散并不能让我产生出胜利的愉悦感,反而让我们共同陷入一种无奈不甘和恐慌。身体呈现的衰老意味着我们渐渐告别前半生的与这个社会的交集,预示着不能再随意拔高跳跃,预示着将失去曾经新鲜旺盛的激情与健康!
虽然强烈的意识到,终有一天我们会随着翻滚的时光愈渐老去,身体一步步步入枯萎,就像之前经历的所有曾经的“失去”一样,但记忆里的母亲却一次次反复感召着鼓励着我们,母亲像一束永不消失的光,晶莹剔亮,照耀在前行的路上。
尽管虚拟式穿行让我的生命现出一道豁口,隐隐露出另一种光亮来,这中光亮是我出生时就熟悉的,也是最让我害怕的……但是相对于这种无法再次回轮的生命过程,我终于紧紧拉起了妹妹的手,告诉妹妹,母亲的爱没有消失,从没有消失,她鼓励着我们与她并肩,一起坚持更稳固地站立在脚下的土地。不要惧怕和埋怨,要明了地探索我们自己的内心。母亲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行路,不是为别的,是出与爱的需要。……在生命短暂的旅途中,生与死只是一个现实的概念,美好的爱真情的善一定会像小人鱼故事描述的那样,会在最后一刻令灵魂蒸腾,存于真空,永不消失!
……
飘那片雪的时候,我是旅人,在广袤的雪地里行走,不同的是世界此刻在寒冷中渐渐变得温暖。
在那片温暖中,我终于再次清晰地看见了母亲,看见了哥哥,看到了大姨大姨夫,朦胧中,我似乎回到了以往岁月,母亲站在开满泡桐花的庭院里慈祥地看着我们,妹妹和我拉着手,此刻正"格格"地笑着……回忆让我如此幸福感动,而醒来,这些亲人像是我生命中匆匆路过的旅人,倏忽不见,我感觉自己又走向了梦里的那个海,海浪翻滚间我再次听到了爱的潮音,两行泪水悄悄蒙住了眼睛,在梦中的那棵菩提树下,我终于再次拉紧妹妹的手,并肩一起,安然有力地,向前走去……
方蕾妈妈是道白月光
是女人,年轻时,总都会有一点儿淑静情怀,和径自领受的精致。衣襟的盘扣要徐徐扣上,偏爱这件衣裳,是因为它像一片白月光。
我总觉得,女人最原始的精致,体现在衣柜里。
很小的时候,爱钻妈妈的衣柜,在一片清凉柔软的布料中仰着脸挑选自己喜欢的,让她穿,或者让她帮我穿。米白碎花的长裙、印着荷叶的旗袍、衣领有花边的垫肩玫红衬衫……那些针脚精致布料柔软的衣裳,透着明艳动人的光亮,却越来越少的被她穿起来,静默又迁就着,成了我扮作美人模样、“粉墨登场”的偌大戏服,使我雀跃、欢喜。
青春岁月里,我迷恋白裙子和一切浅色的、绣着精致小细节的衣裳,我迷恋那种清爽又轻巧的状态,似是行卧白云间。又过了几年,我觉得生活有太多可谈的美学,我歌颂生活,感恩世界。
再后来,我有了自己爱的人,开始布置属于两个年轻人的小家庭,我在白裙子外面系上了围裙。在极平常的一天里,我换下了米色绣着梅枝的宽袖上衣,挑了一件深色的衣裳,系上围裙的那一瞬间,我想起了过往里我曾问过妈妈的一个问题。
我问她,“我给您买白色的裙子、淡蓝色的旗袍好不好啊?”
她说,“我不要,那是小姑娘穿的颜色。”
如今站在庸常生活琐事中的我,才发现,其实那并不是小姑娘才穿的颜色。那只是像曾经的我一样,不去承担生活之重的人,所迷恋的颜色。
而妈妈也并非是不再喜欢那些白月光一样的美好,只是岁月蹉跎,她拿出了所有时间来照顾子女和家人,封闭了自己的精致情怀和女人的纯情。
白色多纯洁,惹人珍重,而生活有尘埃和泥土,妈妈是那个在我享受世界的洁白之物时,静默着喂养我、为我涤洗的人,她才是那最初令我心驰神往的一道白月光,只是经年以后,才被我在一身浮尘中认知。
曾经洁白岁月,都是她的恩赐,情之所至,却羞于口头去跟她说我的感悟,只能写一首诗,发给她——
《洁白岁月》
那是,还在迷恋不食烟火和书面语的岁月
白云翻涌在头顶,白沙细锐
堆向岸边的衣锤。
洗衣裳的妈妈手脚清凉,在我童年的岸边
穿白裙子的我毫无负担。
这洁白的世界,不舍得染我一丝油烟
这干净的世界,令我堂皇,又身轻如燕
而妈妈是长久的稳健,如她藏青的衣着
和钟摆滴答,擦拭着时间、厨房
还有我绣着兰花的衣襟,
以及一种后来才被我认知的
封闭的精致和纯情。
没有女人不爱清晨的白牛奶,
没有人真正不愿意在白月光里横卧着,
心无挂碍地数过星辰
那时我领受着妈妈给予的洁白
却感恩着一个世界的干净
如今我依旧迷恋洁白的事物,但感恩的不只是世界,还有一切,在我身旁为我疏散尘埃的人。
潘莉红
春来满庭芳
春来芳草绿,花开自然香。又是槐花芬芳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一丝丝的甜香,沁人心脾。
今天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孩子,你今天中午能回来吗?我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洋槐花,给你蒸着吃……”
一听声音,我就知道对方打错了电话。她的声音很慈祥,很像我的妈妈。
“阿姨,我不是你的孩子,你打错电话了。”
“哦!什么?我打错了啊,对不起啊,我就一个人在家,人老眼花,按错键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老人家连说几个对不起。我没有先挂她的电话,她也没有挂断我的电话。就这样持续着……我知道她和我的妈妈一样,一定会把耳朵贴在手机上一直在听。果不其然,一分钟后,老人家说“孩子,不打扰你了,再见。”
接了这个拨错的电话,又想到了我的母亲。我的心久久平静不下。自从父亲去世之后,母亲的快乐就是下象棋。母亲一直珍藏一个木制的老匣子,里面是父亲亲手做的一副象棋,这副象棋承载着母亲对父亲剪不断的记忆和思念。象棋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父亲一刀一刀雕刻出来的。父亲生前每天都会和母亲对弈,虽然下象棋的时候避免不了争吵,但是父亲总会让几步棋给母亲。父亲走后,母亲一直和哥嫂同住,哥哥就开始陪母亲下棋,但是哥哥工作很忙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于是,我就在平板电脑上下载了中国象棋游戏,从此母亲吃饭的时间都捧着平板下象棋。她嘴里还不停地叨念着“当头炮”“拱卒”“将军”……每当赢棋了就招手让我们看“快来快来,我打败了电脑啦!”她以此为乐。
母亲有一台老式缝纫机,在我的记忆里都是父亲负责裁剪,母亲负责缝纫。母亲针线活好,她最拿手的就是在衣服上打“盘扣”,打得快而漂亮。母亲说最简单的就是“一字扣”,母亲把平纹布对折用剪刀裁成两公分宽的斜条,用针线把一头固定,再用针把两边的毛边往中间折叠好缝在一起,就形成了很结实的绳,随着母亲的灵巧的双手绕来绕去,“琵琶扣”、“蝴蝶扣”、“蜻蜓扣”,像变魔法一样在母亲的手里诞生了。
母亲不仅盘扣打得好,平时也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每次看见她养的漂亮花儿我就掏出手机,拍几张照片发到
自从有了北京中科医院是骗子北京的最好白癜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