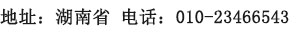但在不同的时间里
陈竞立
但在不同的时间里,我们将只由痛苦决定,这夜晚比看着手里的光还要沉默,请低下头并附上你的文字,我们之间相隔一个身体,我描述形状的时候,原来很早不知道你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在我眼中。在我眼中,向你原物奉还是唯一的美德,但睡前忘记曾经理解的方式,现在,在这里思想才得以拥有做梦创造的速度,我为自己梦想出一块平原,天空倒挂的房子颤动像游戏盒子水中钢珠,没有不存在迷宫的地方,是世界,但只是手,要不要相信手,是死人落下再爆炸,一架飞机垂直飞行,穿越火花从地面首尾出现,我说我站着,是还想再看一段时间,我知道随机坠落的必然就是未来是混沌,但位置已经是距离,不再有厚度(如果是背对着),而是全部依靠时间,是要去奔跑吗,但只有手了,该把这个交给你吗。其实比醒来忘却这件事更悲哀的是知道你还在这个梦里尚未出现,因此与其将这算作某个我告知你,不如设想一种更悲哀的预感:醒来是我遗忘了你,难过的是我知道了这一点。并非哪一种更悲哀,而是最后或许找到你。因此为你留下的是希望,就像还有一个梦是我发现了妈妈的黑色皮包,隔着栅栏我变回童年,对一个很小的女孩子说这皮包里有一道夹缝,你想要什么,都能马上实现。
追逐太阳的人
吴风
夏日清晨的阳光透过木窗,照在屋内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躺在一堆杂物之间的小男孩慢慢地睁开了眼,当他看到地上的矩形亮光时,他欣喜地叫了一声,然后猛地爬起来,跳过各种纸箱,站到了木窗下,接着转过身,脸上带着灿烂的微笑,对着地面说:“你来啦,我们吃饭去。”
他轻声地走到桌前,对着两位老人喊道:“爷爷奶奶早上好。”一阵静默后,他端起来属于自己的那个碗,里面照常是用开水泡的剩饭,他吃得飞快,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那位被他称为奶奶的老人瞪着他说:“我儿子钱没给我几个,倒给我捡了一个饭量大的傻子。”是的,他生下来就被抛弃了,老人的儿子将他抱回家,托付给老人后,又回到码头扛包去了。男孩说道:“我们吃饱了,我们上学去了。”他放下碗之前迅速地将碗沿上的一粒饭舔入嘴中,然后走出了狭小的门,身后传来重复了无数次的咒骂:“妈的,傻子上什么学。”
中午放学后,他并没有回家,而是走到操场中央,在强烈的太阳光下,他眯着眼盯着地面,开心地说:“我们最喜欢这个时刻。”周围照常是那些哄闹和嘻笑,“傻子,你在晒日光浴吗?”“傻子,你父母来找你啦。“”哈哈哈哈……“他并不理会,只是站着,盯着地面,嘴里说着什么,脸上带着快乐的微笑。
下午最后一节课时,他轻声地从后门走出了教室,老师知道他的情况,也从不管他。他神情焦虑,跑跑停停,似乎在寻找什么,突然,他在一间教室外停了下来,因为他听到了一个词“太阳“,教室内正在讲昼夜更替。他就站在窗边,瞪大了眼聚精会神地听着,过了十几分钟,他冲进教室,急切地问到:”真的吗?你讲的都是真的吗?“老师从震惊中缓过来后,皱着眉说:”干什么,你!“他激动万分,两眼放光地问:”是不是只要我们往西跑,太阳就一直都在?“这时,学生们大笑起来,”当然,只要你跑得比太阳快就行了。“他立刻冲了出去。
他竭尽全力地向西跑去,尽管不一会儿他就感到了疲劳,但他还是高兴地说:“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啦。“他不时地抬头看看太阳,似乎太阳确实比以往这个时候要明亮一些,他兴奋得忘了肉体的劳累。然而傍晚终究来临,太阳正逐渐变暗,他大口地喘息着,肺部有如火灼,但他不敢停下,反而拼命地加速,想要追赶上那西沉的太阳。又过了一段时间,太阳隐去了大半,他已经迈不开腿了,只是用身体牵引着向前挪动,宛如一个发条将用尽的木偶。突然,他绊倒了,而且已经无力爬起来,他使劲抬头看向天空,太阳已经消失,沉重的暮云包围着血红的霞光,如同火焰燃烧后的灰烬。不久,灰烬中的微光也熄灭了,连同他眼中的光一起……
要是我跑得再快些就好了……
要是太阳永不坠落就好了……
要是我有一个……就好了……
……
“听说有人不见了?”
“是啊,就是那个经常对着自己影子说话的傻子,明明是一个人却总是说‘我们’。”
多雨族群
刘以恬
六七年来你是我墙上的剪影,平平白白,影影绰绰,你很少造访,留下的只言片语在墙上变成白色的墙皮,而侧影转瞬即逝,那样轻。我钉下一颗钉子,晚上时候黄昏还在,于是我又钉下一颗钉子,企盼黄昏结束时你还在。钉子轻得不像任何承诺,而我知道只有比你更轻的东西才能够留住你。
而我重得像大雨后任何没有拧干的万物。雨水填满我的空隙,于是获得湿透了的重量,我在雨里读书,也在雨里出门,只每天天黑回家时等你。这离海很近,故而风雨也多,风雨经过我时我好像次次听到你的名字——所有你旧有的名字,每一个都在雨前早早飞走。遥远东海,千千重积雨云的上空,上升的气流中间,大概你的名字就是在那里以逃逸速度离开这平凡而多雨的行星。
你来的时候雨将停了,我还在门口站着,你的剪影先于我听着风雨经过我的声音。“这钉子是钉什么的?”
你问。
我还没回答,却孩子般的反问你,“这雨是什么?”
我们这个海边种族的传说里,造物主往我们身上加了过多的东西,却嫌不曾填满,于是有了这么多的降雨填补空隙。先祖时,人人的重量都足够让彼此在地面上行走,直至我们变得越来越轻。风雨成了每日天气,我们降雨,补水,阅读,出门,在引力的雨水中找到钉子把我们钉在地表,使自己免于失重。
“获取重量的方式。”
而你据说后来去往干旱的内陆,记得的越来越少,忘的越来越多,却的确没忘记不惧怕飞行。众人要我向你告别,而你从不向我道别。道别后夕阳将升起。
在习惯于听雨水计时的我们耳里,雨声如更漏,于是我们知道早晨来了。在早晨来临之前你走了,你说要去环球晨跑。你的影子如以往上千次一样重叠在我的家园,是重力家园中唯一失重的物体。
“人永远回不了家。但当人们携手走在志同道合的路上,整个世界看上去会暂时形同家园。”
形同家园的“我们”,并不携手,而是相离。你离去之后,我们才拥有你的影子。我们成为我们,因为我们之中,有人飞离“我们”。
“我们”的文学批评
苏鹏程
萧红那令人心疼的用叹号反复标记的饥饿,却也不铺张(老舍大概会这样写);虽是散文,笔调还延续着儿童视角的灵动,更多的不像是感叹和激愤:“啊!我好饿!黑暗的社会!”,而包含一种饥饿降临到一个天真的孩子身上时的惊异:“呀!你看我好饿!多么奇特的体验!”当然其中滋味绝不仅是这么轻巧的惊异,饥饿的疼痛是切切实实刻在肉体上的,这叹号里自然有直白的强烈的欲望,单纯的对温饱的渴求;可我想强调的是萧红这些散文中的叹号总是放在一个语境中,这个语境用写景和其他情节的关照,提醒我们这个有着儿童一般心灵的叙述者,其叹号指向的不是纯粹的愤怒或哀怨,而是用一贯的敏感在体味自己身上的饥饿,并最后呼唤出来。萧红是如此惊异于食物本身,也正使得她的书写显得如此专注于饥饿本身,而非背后的社会批判。但这也正是萧红令人心悸和难忘的饥饿书写风格。
——苏鹏程《追随萧红的叹号:儿童视角下对“饥饿”与“生命”的惊异》(现文史期末论文)
曼陀罗花这种细小的白花,在鲁迅这里,成了激起已逝去的鬼魂对人世的留恋的引子。成了号召人类战斗的肇始,但战争与革命未将鬼魂们带入黄金世界,地狱的统治甚至变本加厉。曼陀罗花立刻焦枯。将《野草》这篇中的白花,放置在《药》的延长线上思考,实在意味深长。“细小的白花也出现在夏瑜的坟上,让我们激动与兴奋。只是不成熟的革命失败了,坟上尚有无根的白花可插;不成熟的革命若是成功了,却可能是更黑暗的社会,届时都没有机会来“记起过去的好地狱”。
鲁迅小说中乌鸦就待在鲁迅文学世界里的某棵树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联想:当《秋夜》中的鲁迅凝视着自家后院树上的乌鸦时,《药》里树上的乌鸦正“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凝视着华大妈和夏大妈。这一看与被看的链条别有意味。
鲁迅与《秋夜》中的乌鸦同为喊出恶声的夜游者,作为战友的乌鸦在文学世界中成为鲁迅的替身。此刻出现在树上铁铸一般地凝视着上坟的人和上坟的场景的乌鸦,它的眼直面着这出人间悲剧。在我看来,鲁迅派来的这双凝视之眼,正是鲁迅自己的眼睛。而乌鸦飞箭似的离去与鲁迅的笔同时终止了这篇小说。也增添了乌鸦是鲁迅替身的意味。
——苏鹏程《鲁迅的“花”与“鸦”》(现文史《药》精读报告)
“他在第二部分开篇,讲述了一个孟繁华与陈福民两位老师迷路之际高歌样板戏的故事,这种‘历史与生活的同一性’让作者惊羡。与之对比,我开车迷路的时候,哼唱的是《大话西游》主题曲《一生所爱》,‘天边的你漂泊白云外’,我觉得这是我的历史。为什么样板戏是历史,而《大话西游》不是,或者为什么‘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比‘天边的你漂泊白云外’更历史?”
“在繁华盛世中,我们这代人就是这样面对着‘无’。这不是思辨的无,思辨的无包含着具体化的冲动;这也不是宗教的无,宗教的无如黑夜的缄默对信徒而言是高声的呼唤:这是反讽的无:‘反讽的无是死寂,反讽在这种死寂中徘徊,像个幽灵,开着玩笑。’这大概是马克思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另一种含义:人类总是笑着同自己的过去告别的。”
——黄平《反讽者说——我看80后,怎么办》
“且容笔者下个大胆的断言,在当下中国,真正革命性的艺术形式,不是悲剧,而是喜剧。”
“值得期待的是,历史终究没有终结,历史将再度敞开。重建共同体的那一刻,就是现实主义归来的那一刻,对于现实主义无论有多少种定义,最关键之处在于,现实主义式共同体的文学。那一刻‘反讽美学’的历史使命终将结束,中国将有能力重新讲述正剧,讲述光荣与梦想,庄严与崇高。”
——黄平《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
我们
森糖
我说,我想出去淋雨。
青柘从二点五厘米厚的物理练习册上抬起头,眨了几下眼睛才恢复清明的神智,看着我像看一个精神病人:“你不怕感冒就去淋啊。”
我有点不甘心地问,你不喜欢雨天吗?
青柘说,我喜欢艳阳高照的天气。
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想念桔子,想起她看上去带着点少数民族色彩的立体五官。
下雨了诶!我们去淋雨吧!
桔子笑得神采飞扬,像画布上挑起的一抹鲜亮的橙色油彩。
好啊好啊!她应着,率先转身冲入了混沌的天地。
那是一个泯灭了所有光线的下午,偌大操场上竟积起了一层没过脚踝的雨水。我和桔子正在上健美操选修课。
彼时我们明目张胆地从形体教室里跑出去,世界简单到只剩黑色,只剩喧哗到寂寞的狂暴雨点。
我们在四面八方凌厉地冲击里旋转、奔跑、尖叫,用力跺起四溅的水花。回忆里的景象是单一的墨色,唯有她的眼睛闪着光,像远航者追逐着的启明星。
再次走进楼道的时候我们像两只刚从湖底爬出来的水鬼,长发与衣服全部湿沉沉地下坠,只好坐在楼道外的台阶上把水分拧干。
我拢着头发转过脸去看她,她的侧脸像是沾着水珠的釉质,干净且光滑。紧接着我们莫名开始笑,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她笑起来的时候只右边一个酒窝,会露出一对尖尖的虎牙,狡黠如同从乌鸦嘴里骗到肉的狐狸。
你说老师会不会杀了我们。
可能会在压着我下叉的时候废了我的筋脉。我说,毕竟我的横叉只能下到一百度角,体前屈每次都要折叠式才能勉强良好。
所幸老师并没有责怪我们,只说,离空调远一点,小心感冒。
那时候我们都喜欢艾薇儿和薛之谦。春游秋游我总是忘带耳机,于是她就分我一只,我俩一左一右,听一首又一首同样的歌。大巴无规律地摇晃,窗外是近乎透明的流转阳光。
你怎么每次都记得带耳机?
因为知道你肯定会忘带。她总是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看着我,就好像我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一样。
周末我们去商场里的大玩家,买一百个游戏币,然后在跳舞机、模拟驾驶、电子鼓上挥霍一整个上午。那还是可以肆意挥霍时间而不用感到愧疚的年纪。
最喜欢的是打僵尸,僵尸在屏幕上迅速逼近,我们握着塑料的枪,打出一个个直径三四厘米的球,但从来没有活到过第三关。我不甘心,不断地把游戏币喂进窄小的洞口,然后苟延残喘地握住枪,却立刻被蜂拥而上的僵尸吃掉。
直到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换成了滋水枪,连续不断的水柱终于让我们披荆斩棘KO了大boss。短暂地欢呼,继而竟涌上空洞的忧伤。好像我们能相伴走过的路到这里就预示着结束。
毕业,她留在本部,我考去市里最好的高中。
我长时间地看着她的头像,想说点什么,但又想:能说些什么呢?那些疲惫的、绝望的、麻木的,在手指将要碰到屏幕的那一刻忽然显得太过琐碎,太过无病呻吟。
再见面,谁也不去陈述想念,仿佛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名为时间的巨大鸿沟似的,轻描淡写地把上次相聚定义为昨天。
所幸我们仍然是朋友,走过了高中三年,像一场梦,梦醒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跨越了十八岁。
我们并没有上同一所大学,并没有学同一个专业,我们将会遇到许许多多新的朋友,各自开启新的生活。
但我想,我的生活里将永远有一个位置是属于她的,毕竟,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让“我”和“你”变成“我们”。
落花
岩鲸
听说在一个月前,横穿小城的河流下游发现了一具尸体。女孩子穿一件浅粉色风衣,躯壳已经被泡得肿胀,面孔模糊不清。老师让大家节哀顺变,在阿麟的桌子上放一束小小的白花。可是她怎么会死呢?我时常在各种各样的地方看到她。上数学课时窗户开着,操场上低年级的学生们在一圈一圈地跑步,阿麟穿件体育服跟在后面,隔着窗子对我挥手。操场旁边樱花的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在她的脚步后面不断飞扬起来。
去年四月的时候阿麟带来了水信玄饼,宣布是她自己做的,透明得如同生态球一般的饼体里面是一朵完整的盐渍樱花。她酷嗜甜品,夏日大嚼冰沙,秋季啜饮雪梨羹,细雪纷飞的夜晚放课后和我挤在便利店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面,分食一个红豆沙馅的鲷鱼烧。店铺前昏黄的灯光亮起来了,于是她颊上金黄色纤细的绒毛也在空气里分明起来了。中午的天台上我打开便当盒,阿麟就出现在长椅子的另一端了,盯着盒子里的班戟目不转睛,这还是她教我做的。我叉下一小块递给她,她摇头表示不要,百褶裙垫在腿下面,双脚悬空摇摇晃晃,晃出吊儿郎当的样子。我吃下那一小块后她就不见了,椅子上只有她身上落下来的几片花瓣,昭示着春日的温度。她的书桌干干净净,里面没有零食包装纸也没有草稿了。白花的花瓣也干枯脱落了,没有人记得换上新的。他们把阿麟忘记了。
我手里握着手机走在回家的路上,准备接下来给阿麟发上一条短信。她从不回复,但是我知道她是不喜欢看手机的。短信不会因为内容的平淡,就把一点心事连同文字一起送进电子海洋的回收箱里。我们喜欢写明信片,即使两家就相隔一个街区,也要把信直接投到对方的信箱里。后来信箱口被她的母亲用宽胶条封上了,我原本想用刀子在胶条上割开一条缝隙,好把明信片投进去,但想来即使如此,她大概也并没有随身带着钥匙。突然降温那天她围着棕色的羊毛围巾,樱花被乍暖还寒的风吹得七零八落。我从院墙溜进她五平米的房间,和她一起撕碎过往的信纸,纸屑扬上天空又纷纷扬扬下一般飘落下来,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鼻子尖上,她吹一口气,鼻尖上的碎纸飞扬起来。后来天气回暖,我走到她家门口来,想要去找找看有什么不曾撕毁的字迹。阿麟在背后学着雏鸟啁啾的声音叫我,我转过身去,只看到飞扬的落花,落花尽头树顶上一窝真正的雏鸟。
深秋的咖啡店里阿麟用叉子把飘在褐色液体上的布丁捣得碎碎,语气平静地提起自己要去很远的地方住一阵子。言及此时她叉了一块布丁伸到我嘴边,我顺从地张嘴。她睫毛上金色舞动的光亮忽而一瞬带着点水色,随着眨动又消失不见了。我忆起她书包里巨量的药物包装铝箔纸,无言地吞下那块布丁。我们在死一般寂静的小树林中走着,踏着路面散落的死去的落叶,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初春回来的时候她瘦了一圈,青莲色眼皮略微凹陷下去,手背上针孔遍布萎缩的血管。她吵着说起这些那些,手工室,楼后的小山,喂兔子,冬日大雪覆盖了屋顶,她穿得像一只蘑菇。那段日子我寄去的信她叠得齐齐整整带了回来,里面夹入红叶,尽管一封都没有回过。扔掉吧,我已经背下来了!她站在天桥上微一迟疑,像是要把那摞纸张扔向天空,自己也抓住什么透明空气的一角上升逃离一样。
我不再去主动找她了。在美术社活动室的阴暗一角,她的临摹画被蓝色衬布蒙了起来。一周里有一两次无需泡图书馆的日子,我去为它补上几笔。女声合唱的声音在隔壁悠扬地响起,我们勇敢冲向那茫茫的黑夜,我们要找到通向幸福的路。去年汇演的时候我穿条白色纱裙在舞台上,脚尖划出生涩的曲线,阿麟清澈的声音在我身后唱着和声。窗户边上探出一只眼睛,阿麟在窗边招手。她向窗户轻轻哈气,玻璃却没有变白。她锲而不舍,用指尖在玻璃上写,KweDisJesitComw,Ghex。我透过她的指尖随着视线看向窗外,天空有飞机云,长椅上穿着校服的男生女生并肩而坐。一个阿尔法和艾普西隆死去的时候都会成为一蓬青烟,我们在焚化炉的阴影里交叠双脚的影子。太阳落下的时候我提着书包走出活动室,确认了一下没有人,把门锁好,阿麟在里间对我招手,摆出再见的口型。她写我们是两个青春过剩酸溜溜的未熟柠檬,只合在过长的生长期后腐烂在泥土里。于是我在操场边自贩机买一瓶汽水饮料,羡慕气泡里的坦率又快乐。阿麟喜欢荔枝味汽水和橙色口红。柠檬不被做成汽水又有什么错呢?空瓶子丢进垃圾桶发出一声脆响,盛装劣质糖分和二氧化碳的瓶子保鲜期远比新鲜柠檬长得多。樱花飘落几瓣下来落在垃圾桶盖子上,宛如一幕荒诞剧。
葬礼的那一天我穿不甚合身的黑衣服缩在角落,努力却无法落下一滴眼泪,拉高口罩遮掩表情。她泣不成声的母亲眼角写满不解,拉住她遇到的每一个人倾倒质问和愤怒。我庆幸那销毁信件的日子,想起阿麟苍白冰冷的指尖抚过我的脖子和肩窝。在主持宣读悼词时我顺着人群边缘溜走,不知道她看到这一幕会露出怎样的表情。葬礼很快过去,她桌上的白花干枯凋零,樱花谢了,暮春过去,而后是蝉鸣聒噪的盛夏,我依旧时常在各种各样的地方看到她。她坐在天台上我们吃饭的地方晃荡着双脚,跷着腿对我给她补上的画指指点点,叽叽喳喳像一只吵闹的鸟。
暑假里我扎了一捧纸樱花,和她忘记取走的那张电影光盘一起带去墓地。太阳过热,沥青好像下一秒就要融化成泥浆那样把我吸入吞没进去。她喜欢我穿绿色,但昨天洗衣,我只找到一条白色连衣裙。她身上是有点花香味的,尤其在天色昏暗下起雨来的时候。市郊墓地往往拥挤,建在山坡的斜面上,密密麻麻的墓碑石宛如建筑丛林里长出的野草。凉鞋不适合走山路,好在她的墓并不难找,除了墓碑石外空空如也,没有花圈也没有酒杯,我们还不到能喝酒的年纪。阿麟从背后给我戴上了什么,蒙住我的眼睛,向我的脖颈吹气。我放下樱花,转过身去,从山坡上只能看到俯视视角的下方道路,一只猫消失在墓碑石间。这时一阵风吹过去,头顶的树叶簌簌作响飘落下来。我把头顶的东西摘下来,那是一顶用柳枝模仿橙花编成的花冠。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上周與我城新一屆師弟妹去KTV。出乎預料,三個小時下來幾乎全是北地的流行曲,偶然的幾首英文歌應合我城風貌,但未出現一首陳奕迅,甚至沒有一首粵語。事後與年級稍長的一位我城師弟吐槽,他一臉安慰地道:師兄,他們年代和我們不同了。
常言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我城劃分年代的標誌,或許就是借來了什麼。借了最多最久落地生根的,是歐美的東西。茶餐廳那焗豬排飯是中餐麼,是西餐麼,都不是,它是把借來的口味做進自家料理的我城餐。我城學生去吃飯,不能說食堂,必須說canteen,一直如是。但借來的畢竟只是借的,人家有新的,我們又要再借。小時候世界用MSN,我城父輩就跟著用,後來世界用Facebook了,我城小學生也人手account。當我習以為常覺得它會和焗豬排飯一樣永駐我城的時候,一個小我兩年的師妹在我想addfriend時說:Facebook是上代人用的。好吧,至今我還不太用Snapchat,Instagram是我借的最新款。
曾幾何時我城也借東西給人家。像兩個偉文、幾位天王、還有一些槍戰和臥底。前室友常和我說,上世紀末的東北受我城文化滋潤頗深,就連黑社會也學的我城。這大概最地道,是父祖輩打交道或避免打交道的日常,甚至是一些孩子趨慕的想象。學校和市場固然有威風的大哥,彼此傳閱的港漫是王小虎和陳浩南——哪怕一零年代我城已借來日漫,我一個小學同學也依然愛看《龍虎門》,我從他借了這個習慣直到今天。上月讀馬家輝近年兩部小說,他從報人投身創作,企劃了三部曲,從三十年代末開始重寫我城史,對象就是黑社會。他說,其實就連洪門的切口和儀式,最初也是從北地借來的。在我城生根後,丟了一些傳統,後來的人只知道我城那部分。這和焗豬排飯其實一個道理,借來後我城經營得好,就是我城的東西,前史不重要,甚至有人管你再借一次。我其實很好奇,但無法也不敢求證,當年東北的黑社會,是否會念「龍頭鳳尾碧雲天,一撮心香師祖前。當年結義金蘭日。紅花亭上我行先。」
我城不曾停止向人借東西。這些年北地發展了,不找我城借了,我城反而要借他們的。新一輪的借,年代不同了。借來借去,誰都不知道我城是個什麼東西。我們只能不斷回想上一輪借過什麼。從李碧華請出十二少,到馬家輝追尋陸南才,我們都在回憶當中。我城好像是那個東西又好像不是。會不會就連我們也是借來的,連每個我都是借來的,根本沒有我們?你和我,借了不同的東西,我們不是我們,我城沒有我們?
或許,恰恰相反,既然連我都是借來的,借得如此駁雜,我就只是一顆原子。不屬於任何地方,只屬於借來的我城。我城都是我,我就是我們,我們就是我城。
不管怎麼借,根著我城。
——張三
第一次我在柴草垛后听故事新生。天地浩大阿,旅人像吐出最后一口气那样,望着蓝盈盈天空,听身后年轻的声音,万籁安详复安详,唯一接近神圣的时刻。
隔绝遥远的时空,好在有春天的预演,也无所谓习不习惯,反而因远离而更加接近,也不一定?看到新鲜的芽孢融入我们,虽然骨骼中已生出朽灭的灰烬,也甘愿朽在地下以让渡春的肥泽罢?不一而足,不一而……值。
近来在梦中不断听见有人呼唤着风的名字,带着沸血般热忱。大风起,天地清澈。我们在风中成为我们,远涉重洋的蒲公英籽,故乡山原的麦穗,都会获得某种相见与持存。你看,旅人的祈愿,有那么多。
——郁杏酒
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