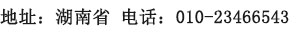母狮女神巴黎堆满了镶着金边的镜子,店面规划精细,博物馆星罗棋布,部分街巷铺上鹅卵石。马赛则是一阵凛冽的风,刮走了繁文缛节和传统礼俗,余下的空间都塞满了行色匆匆的阿拉伯移民劳工。马赛的粗犷便是其迷人之处。19世纪的莫泊桑写道,马赛“在艳阳下挥洒汗水,好似有恃无恐、不惜容颜的美少女”。马赛让我明白,在地中海的历史中,权力第一,美丽次之。我在卢浮宫见到的艺术品都是富庶大国的产物,富庶大国往往先精于繁荣贸易和军事战备,而后才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除了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称之为“罗马荡平霸权”阶段(公元前年罗马彻底扫荡迦太基之后的阶段)之外,从远古到中世纪,地中海地区一直都是政治权力制衡的范本。贫瘠的沙土让这里的人们不得不出境南征北战,然而无论是迦太基人、希腊人、汪达尔人、拜占庭人、威尼斯人还是土耳其人,无人能掌控整片地中海。我眼前的这座城市便是那段动荡历史的复刻品:来自北非的阿拉伯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希腊人、科西嘉人以及其他地区的移民,纷纷涌入这个街道脏乱、社会秩序和商贸活动被破坏的地方,马赛成为地中海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在不合时宜的季节走进一座城市,如同见到在家裹着浴袍却浓妆艳抹的女人,既亲切又失落,或能让人从中有所感悟。英国的地中海研究权威帕特里克·雷·费莫尔写道:“不同于夏日短居,冬日小住给人以光荣的居民之感。”由此,对人类而言,地中海并非一片完整的海域,而是系列小水域的组合——亚得里亚海、爱琴海、第勒尼安海等,每一片水域都有其自身迷人的魅力。往往海域越是狭小,其历史影响就越是远大,因为人类能够掌控小片海域,并在其间留下活动痕迹。阅读如同一场外科手术:解剖四周环境及自身的旅行动机。灰之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维吉尔的埃涅阿斯以其远大理想鼓舞我们奋进;在和平安详的年代,荷马则更旗帜鲜明地向我们彰显了英勇斗争的朝气与活力。那个冬天,随着我渡过的海域越广阔,我对这两本史诗的兴趣就越发浓厚——传奇故事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催化剂。夜色下的海呈现出几近墨色的深蓝。两座离岸小岛——法维尼亚纳岛和莱万佐岛——在海面浮现,如同神话般引人遐想:在虚无缥渺的不真实感之中,它们不像真切的风景,更像人们心中的回忆。破晓时分柔和的光揭开了杏树的面纱,露出树上淡紫的杏花。劲风刮过,沙尘突然消失,一切呈现出大雨冲刷后的明净。欧洲展现在眼前,非洲已在身后。旅行是孤独的最佳形式,因为真正的探险不在于身体的磨难,而在于知识的汲取。西西里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也是地中海东西两面的防波堤。西西里岛不仅属于欧洲和非洲,还是希腊和拉丁世界的交汇处。强大的地中海文明都曾占据西西里,并留下足迹,其中有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汪达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以法国诺曼人为代表的欧洲种族。埃里切山是常年被浓雾包裹的遗迹,浓雾时聚时散,哥特式的正门也时隐时现。哥特式风格可以圣马蒂诺教堂为例,过去是暗红系,如今则在水浸烟熏下褪为粉色,诺曼或哥特式风格的墙面被千百年的风风雨雨剥蚀。这里是窃窃私语的地方:阳光明媚的地中海之心被囚禁在寒苦凄冷的黑暗之中。缄默的神殿乡间的浅谷和山丘搭配,看起来好像一辆平缓起伏的云霄飞车。嫩绿和亮黄的橄榄园与麦田之间缀有水流湍急的沟渠,桃金娘和龙舌兰夹杂在其间。沿途,我们听着羊铃叮当作响。神殿隐约在远方现身,仿佛一个秘密守护者的暗灰身影。居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艺术批评家伯纳德·贝伦森称之为“自然中混沌、漠然和无序之下的理性、秩序与智识的象征”;歌德描述过“风在有如森林的石柱间呐喊……”的画面。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我禁不住想起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向越南共和国提供少量军事援助后,约翰逊总统却增派了50万名美国军人前往越南战场。雅典在西西里的遭遇和美国参与越战之间的偶合十分有意思。就在我前往地中海的半年后,美国灰头土脸地从越南撤军。而雅典的远征军也很快遭遇了难题。摩里亚半岛与新柏拉图主义古典学者艾迪斯·汉弥尔顿写道:“希腊人的独特在于能在透彻洞察世界的同时发现世界的美。”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是最为稳定而合理的伴侣:参见欧里庇得斯的剧作以及果戈理、康拉德的作品,其中巴洛克式的人物及景色皆是通向悲伤结局的媒介。像普列松这样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希望通过一种高于个人的神秘秩序来加强希腊的民族性,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都市社会中的个人权利。辩论的结果与两方的意图都相反。尽管这场争论从未得到解决,但它在整个希腊古典思想的兴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在马基雅弗利和其他文艺复兴思想家的作品中开花结果。普列松并没有通过异教复兴东正教,而是彻底摧毁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概念进程的一部分,取而代之的是科学和世俗政治。点击上方链接购买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抽取2人各赠送1本《地中海三千年》
注意:活动仅面向爱知学者用户,中奖后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