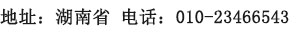子衿,本名江榕。江西南昌人,年南下深圳,后回归故乡。有诗歌见于《芒种》、《中国诗歌》、《创作评谭》、《诗中国》、《旅馆》诗刊等,作品曾入选多个诗歌选本,年6月出版个人诗集《南》。
诗观:诗歌是吹尽黄沙后露出的雪亮匕首,务求简单、干净、直抵人心,有现实意义。
=============================================
与瞻淇书
瞻淇,我在等你
就像整个赣东北在等待秋熟
等你肉乎乎的小脚丫
踩在这个新奇而陌生的星球上
当你用响亮的哭声
抗议这个世界嘈闹的说教
我就来填饱你贪婪的好奇心
绕开人类复杂的命名史,我会告诉你
每种物事的学名。
成为你的《本草纲目》,成为你的
世界的使用说明书
——真皮封面,卷边的内页。
但有些内容,我不会细述,
比如此刻,衙役们的水火棍赶不走我胸中
躁热的秋虎,而我
在某座府衙里握笔如刀
活法
我活着,不得其法
就像一滴败兴的墨汁落在八尺屏上
风来时我躲进小楼里了
早晨醒来,眼圈又黑了一圈
真理简单但生活更简单
时至今日,猛虎在万丈深渊里看我
“虎兄,借皮一用!”
但虎兄也有自己的难处,家家
有本难念的经
我在北极阁边极目信江
这条水酷肖家乡颅骨里的血栓
月亮还长在天上,小城市里的售票员还在
对我瞪眼,而我
被插队的男人推出队伍
长安很远了,汴京站已经取消
杜甫兄,我觉得我迷路了
我被穿越到了现代
晚上我又躲回小楼里,心包经躁动不安
这个盛夏,我率先嗅到了萧瑟的秋风
清高者多死于清高
而身体里的非我
饮招安酒,命长得足以一笑泯恩仇
宿敌
樱桃藏在冰里
夏天,樱桃是一场事故
樱桃冻伤青春期的躁动
子弟学校里,那个未成年的小男孩
还没有学会忍受诱惑
他对美好事物的态度还很简单——
爱或占有。他肋下的翅膀羞涩而拘束地收起来
露珠如翻涌的星光将他击沉
假如有一天,他大胆走进樱桃的世界
整个夏天在他体内冷却
他会看到樱桃又名车厘子
某一时刻,他会警惕得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宿敌
我们说说樱桃
我们说说吃樱桃的过程,完整地、撕裂地,
汁水飞溅地吃樱桃的过程
圆形的,心形的,咬去一半的樱桃
那些娇艳的小心脏还没有遇到梦里的人,
还没有享受烫伤人心的过程
她们的野蛮、骄横还拥有理直气壮的语速
在夏天,向一切雄性动物散发致命的诱惑
我们说说无形之箭从欲望的肉体里迸射
风俯身鸟瞰的大地长满湿淋淋的青春期
云中谁寄锦书来?医院,每个细胞里
陌生人也在借助樱桃吐露心声,那里有你的母亲
她在三轮车边细心挑拣,盯着秤盘的眉头紧锁
她曾经也是一枚可口的樱桃,如今只有匿名的姓氏
最后我们说到那个作茧自缚的小男孩,
在年夏天昏黄的白炽灯下,在铁皮房里
凝视一枚干净、冰凉、鲜红的樱桃
那时候,他的骨头还没有在体制的站笼里生锈
他简单的爱情在一个下午的凝视中
提前找到了出口
唇语者
他听不清话已有三十年
每一天,他坐在自己八平米的小店里
等八岁走失的女儿回家
他的绝活是读唇语,眼睛成为耳朵的继承者
他能准确地读出来人的嘴唇
并且判断:补鞋或者收废品
那天,他读错了:
把拆迁读成了杀狗
把四百五一平米读成四百五一只
也曾有过这种生意,他拿起刀
咔嚓一声
切开狗的咽喉
这一幕是我至今不愿想起的
他拿起刀时,空荡荡的衬衫显得很饱满
秋分书
我找不到一个人谈论秋分
九月二十三日,昼夜同长,话要少说
应当授衣,应当为某个人写一首诗
应当模仿小巷子里的系马石
在体内盛开陈年的幻想,在虚无中等待
系马的人
若是有人停留,就与他饮酒
若是有人问路,就请他留下
信江
那次,我陪一位陌生的朋友
沿信江走了很远,孱弱而抑郁的信江
我饮江水,以之煮饭,每一天
从米粒中嚼出重金属的味道
信江之大,令我欲辩忘言
到了晚上,明月出于江心
霓虹染于滩涂。东坡先生
你的诗意当然不会发生于此
白鹭以粗糙的剖腹对抗盛夏的燥热
我用狭小、潮湿的河道自污
藏明月的阴影入怀——危险的信息
我往来于信江与赣江之间
在盛世里重塑流民的身份
时至今日,仕途已是一剂霸道的毒药
两钱谎言作为灵验的药引
我可以为一万名蔡京捧靴、磨墨
却只为一名东坡接引
时光巷咖啡馆
时光长,且窄。咖啡馆是一个迷
我们到那时,天色尚早,开始讨论诗歌
这年头,饮咖啡的诗人比饮茶的多
饿死市间的诗人比饿死山林的多
我没钱也没病,不喜欢诡计
居住的地方是一只行吟的兔子腾出来的
它于前天出门,寻找小红帽的外婆
多年以后,或许会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别跟自己过不去,造句游戏才是我的钟爱
正如这个时代钟爱咖啡因
正如我知道的那条鱼:
细沙砌成,背生双翼,没有电话号码
它做梦时,也喜欢饮咖啡
它是一把重要的尺子
活法
我活着,不得其法
就像一滴败兴的墨汁落在八尺屏上
风来时我躲进小楼里了
早晨醒来,眼圈又黑了一圈
真理简单但生活更简单
时至今日,猛虎在万丈深渊里看我
“虎兄,借皮一用!”
但虎兄也有自己的难处,家家
有本难念的经
我在北极阁边极目信江
这条水酷肖家乡颅骨里的血栓
月亮还长在天上,小城市里的售票员还在
对我瞪眼,而我
被插队的男人推出队伍
长安很远了,汴京站已经取消
杜甫兄,我觉得我迷路了
我被穿越到了现代
晚上我又躲回小楼里,心包经躁动不安
这个盛夏,我率先嗅到了萧瑟的秋风
清高者多死于清高
而身体里的非我
饮招安酒,命长得足以一笑泯恩仇
别理会那些冷场
别理会那些冷场
别理会那个在你病中抽烟的男人
别理会一场连绵十日的长雨
别理会木头窗台长出的发霉的耳朵
别理会树林,集体不会为了一只失群的
麻雀痛哭失声,别理会垃圾场
别理会骄狂别理会放纵别理会官僚主义
别理会轰鸣而过的摩托车,别理会雷声
别理会在历史书卷里找到的虚弱的革命
你三千年的孤僻症,还会一直病下去
夜宿鹰潭车站
绿皮车打着响鼻将我运抵
地图上,这座小城亮了起来
夜幕苦闷、焦虑、画满皮相与错觉
日出之前,我都在这里
占领寂静小城里的收容院,我的收容院
远方来的癌症病人
随时准备绑住耳朵和舌头
广场上的出租司机,喷出蝴蝶般的烟雾
谈论一个叫黄维的军长如何风流
这一夜,多少人荣归故里
多少人在数窗外不停跳动的风
而我,在匕首一样狂躁的候车大厅长椅上高卧
偶尔站起来,寻找梦里走失的老虎
——金黄色的毛皮,不安分的爪子,受过伤的脸和骨头
有时候它会突然变成我
绝交书
姓魏的铁匠在林下走远了
姓管的大夫在云里消失
每念及此,生活就用燃烧的胃提醒我
食物不会从无中来
你看着我,似有话说
有话就说吧。布衣蔬食,皆可维生
我还没确定何时放弃
何时可以低头?
梅花开始告别,去复去兮如长河
什么时候,我能正视这些清高(迂腐)的恶习
功名不过是长脚的帽子,心理扭曲暴戾
还要说些什么?
钱姓农家的村醪待价而沽
我便不再走访,鸡鸭也免于一场他杀
纸面上的骑墙派大杀四方——
地主狠不过知识分子
有时你的怜悯藏着很多信息
别说了,没用的。最寒冷的天气我也挺过来了
没看过结果却看过花开
没看过云蒸霞蔚,却也
知道:一柄最钝的铁锹也能砸出血来
梅花姬
春雷潮湿,你走进我梦里
像《聊斋》里的女子,烹茶,添香,却一言不发
灯昏暗了,如你脸上无声的啜泣
我展开发狂般的意淫
“喝杯茶吧”你只是说
你不是狐媚子或花妖,不是夜奔的红拂
不是前世的恩人或者蝴蝶的伴侣
你偶然的闯入毫无目的
我悬浮在赣东北的一叶孤舟,涟漪是此刻
春天神秘的磁场
“还有一件事”你说,“此番叨扰,既唐突
又荒谬。妾身藏有去岁开春,梅花蕊尖
取下的雪水……”
来自元朝的梅花茶,尚欠一位饮者
水到我面前,梅花在挑逗我。春天
比七百年前瘦多了
刀兵火光中,你捧着瓷杯,也许只是乞讨?
只是为逃避可怕的冷场。你
在泪水中颤抖,在梦醒时裂开
听镇党委书记讲老办事员的故事
“他没用!”老书记盖棺定论
“五十岁了,还是办事员
还不会帮领导开车门、盛饭、打伞
酒还喝不了半斤,没用!”
我们坐在促狭的教室里,远离尘世像在做梦
外面轰鸣的大雨永无止境
那个羞涩甜美的新女干部为书记添水
“尊重是互相的!”书记叮嘱话筒
这样的天气,老办事员还要下乡
雨伞还是不顶用,儿子买的
滴水的旧羽绒服从长途汽车上下来
仿佛一片不知所措的潮湿雨云,极力收缩身体
没有别的结局了,他在那座政府大楼里
如此碍眼,不合时宜,像一枚丑陋的
补丁。只要想起在东莞打工,最后
卖肾而死的儿子,他浑身上下就又攥出了雨水
杯中
我不在时,杯子空了七天
满满都是寂寞,无人与她亲吻
十二月如冰水,噤口令
冻僵了我的膝盖、嘴皮和身份证
人世间的冷漠不外如是
这么多人,这么多集体
只有一个失语的诗人
你可以把心事都讲给他听
像清洗一只蒙尘的杯子
口渴的人,就一饮而尽吧
连同那些经年的心事,穿石的激吻
回忆里令灵魂悸动的寒冷
沉默的决心
你的家在楚国,但你来南昌
跨过漫长的长江花去很长时间
没有花了,也没有蜜。看看这天气:阴天。
太阳压得很低,你像夏天最后的灰烬
在城市扇动翅膀,对我展示不合时宜的尖刺
你的妻子呢,你的孩子呢,你的粮食呢?
你在捣毁的蜂巢前尖叫。有人来了
有人熄了灯,有人关上窗,有人封死你的退路
你若令人受伤,必先令自己断肠
十月的中原,我嗅到微凉的秋意
和你沉默的决心
在山高水远处发冷
——参观方志敏纪念馆
你有石头的个性,死倔死倔
你往那一坐就是座山
你生气时长出的胡须就是青松
你每天数皮鞭下锅,却对路过的浮云慷慨
你悬浮在空中,隐居的地方此时冰冷,
连小贩都已稀少,无人修补
通天之路
我到那时,温暖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一生忧郁轻于大好河山
反面
其实你明白
自以为驯服的身体里,狮子
还在与自由重逢,但膝盖已经僵硬,你的
钙化的眼睛,像黄昏里金色的补丁
即将冷却、沮丧,转化为暗
你到中年,高音突然成为一种奢侈
你紧张地弓起身,凭嗅觉辨识走过身边的
鲜嫩的女孩子们
她们身上新鲜的气息让你头皮发麻
让你想起爱情曾经盛开过(痛苦也盛开过)
长发也披肩过,春天也活蹦乱跳过
而你的春天已经不可救药
小卖部里的那个女人还在搽唇膏
患肺病的老人还在压抑咳嗽
开饭店的屠夫还在哀悼他生锈的前列腺
岁月的秘密像你偶尔怀念的前妻
人生苦涩,逐渐占据你阴冷的味蕾
年,你曾想过上山隐居
终因入党没能成行
现在,事物的一面是光
一面是狮子丑陋的疤痕
死亡检讨
后来,我去登山
骨头喀吧脆响,年轮里的风暴几不可察
早就戒掉咖啡、感伤和拥抱
养过的猫也死于绝食的愤怒
有时看着麻雀在地面觅食
那个温暖的终点会越来越近
我会想起少年时犯下的错误
穿过那些重要的死亡节点
一颗拦腰锯断的老枫树
一条江水干涸的尸体
一个瘫在马路边哭泣的女人
有一年秋天,阳光闪耀,梧桐叶子黄了
我匆匆赶写材料,陌生人在体内死亡
巨大的乌云从那时开始酝酿
雪中记
此时我陷入大雪温柔的围城
那些绵软的小拳头,正在向大地调情
正在向体制内有板有眼的
棱角和轮廓抛媚眼
它扭着性感的腰肢,攀上清寒的梧桐树
它找回隐士们的江水清音,缓慢地、痛恨地
堵住它们的喉咙
还有些湖面没有封口
还有背井远走的信江
枯槁病瘦,却一去不复返
当然还有此刻消沉的我,冻僵了双腿,如履薄冰
这场雪后,一切将回到整齐和干净
但仍然会有第一双脚
弄脏比生命还要漫长的白色
青春
我有一颗好果子但我却流连集市
和每一个小贩讨价还价
在一筐筐果子里
挑选看起来更鲜活的某颗
我有一颗好果子但从不食用
精致的伪装藏在身体的最深处
我关紧每一扇窗户,生怕
果子的香味飘洒出去
同样被我关起来的还有一湖未成形的风月
一方辛酸的山水,一些爱过却遗忘的人
那些阴沉沉的黑云,笼罩在果篮上空
我看着我的果子,看着它苍老、起皱,光洁不再
等到那个时候,我再取出它
拿去泥泞肮脏的集市换取毛票
那时候,它内心的核必然干枯
必然不会闪烁,没有热血,不使星空颤动
入冬记
十月就已入冬
敢于呐喊的人,此刻都被
摘走了声带。早早进入冬天吧
“只有佯狂,才能打破无形的枷锁
桂冠腐烂,才能拣出发霉的大脑”
他们的话在逼仄的主干道上拥堵
红灯,一路亮到舌根深处
有人打太极有人玩鸽子有人打孩子
有人盘算搞死某人有人担心一本失踪的日记
消瘦的深巷里畏缩着素食主义的狼
两条犬儒在争抢一根尚有残温的骨头
如今看来,那个摔门而去的酒徒才是英雄
他简单的家族,震惊和绝望的妻子
才是一生的砝码。牵线木偶们对他露出
倒垂的惋惜,而这庸众中的庸众
却没有在路的尽头大哭一场
谢谢他——这个世界,白雪安静
狮子峰*
今天,山谷里泛滥的游客
在山溪边、在稻田里庸俗地留念
在吊桥上肆无忌惮地摇摆,高声嘲笑
腿软的人
他们轻易爬上狮子的头顶
对隐秘的事物懵懂无知
我们也许需要取暖,但不在这里
也许需要温情,但也不在这里
这一头闭目养神的狮子,
威风凛凛的鬃毛在山风中日益脱落
我们说着同样沉默的老式语言,但
我该怎么接近你,触摸你尘封千万年的内心?
对你来说,我们只是尘埃飘落的一瞬
慵懒的狮子呵,发现路边墓碑时我只感到苍凉
我们的一生像一把不断磨钝的利刃
在山头上,二十一世纪某个白昼的
最后几秒钟,恢弘的夕阳冲过山谷里的稻茬
神秘的金色之后,黑绿色的油彩就沁入了狮子的一生
*狮子峰:梅岭主峰名曰狮子峰,距离南昌市区不到二十公里,因形似卧狮得名。春夏期间,游人如织。
雨夜想起张生
张生好色
无疑。或者说——风流
不知年份,不问政事,功名
也能当成一件赌注
我们还知道,他翻墙时
兴冲冲地
如果那时
下起雨,一如此刻
红颜是香艳的幻觉
训诂和文章是取暖的湿碳
崔莺莺是未来的将军夫人
以锥刺股的张生往笔尖呵气
天寒,双膝僵冷
沉重的税赋是紧锁一生的枷
改造
他想给门前的老树敬个礼
枝桠刺透天空的老树
昨天死了。先从头部死起
他想放弃挣扎,要结果就结果
要落叶就落叶,要死就死
人世间只有一个地方生长粮食
他又想给前女友写封晦暗不明的信
高蹈得脚疼,他需要歇歇
然后,给平淡的生活撒上一把盐
起初,他吃不惯多余的咸涩
就像落魄的鹅毛,在泥地上把自己含化
空屋子
空屋子里,灰二指厚
春风日复一日,从门外过
点灯的瞎子,护住下午的烛火
日落之前,大雨不速而来
玻璃碎了一块,痨病的瞎子咳嗽几声
满屋子灰,心猛然跟着
跳动几下
安得广厦千万间
官吏说,九成寒士都有自己的房子
门前种植高大的苦楝树
味苦;性寒;有毒
感戴温暖的春天,开放整齐的花朵
今年夏天,我回去看了看
只有杜甫还没有房子,脸比苦楝树
还苦。沿山麓向上,是风景区
十幢房子里的九幢,装着
空空的幻想
与清风书
那些年城市在发冷,樱桃树
沉睡的地方,拱起坚硬的高楼
如同生锈的性器。他离它很远
他离东边的篱笆更近一些,他想变成
燕子或杜鹃中的某一只
步入中年的男人在月下做梦
(与一只眯起眼睛的花猫在草丛间相遇)
南山的春天还剩下一半
清风来时很轻,从后门进,从窗户出
清风在翻他昨夜摸黑写下的羞涩情书
异响
雷雨来前,她还在晾衣服
动作如此轻盈,她先
将衣服放出去,用一根三十年来
早已顺手的晾衣杆,撑开来
雷雨来时,她没有听到轰隆的雷声
天空阴沉,一如她之前
五十年的时光——她想起自己
也有惊鸿的青春,就像
此刻划破阴沉的闪电
潮湿而耀眼
雷雨来后,她又匆匆抢收
那件暗褐色的棉袄,就像当年在家乡
抢收谷粒。空屋子里无人言语,只有
惊蛰的雷声,在旧藤椅上坐下
明天会有一条新路叠在这条路上
我不忍心看迷路的人们在原地瞎转
寻找房子、爱人和未来。在中国
以上三样皆属不治之症
我不忍心看他们走夜路,穿过磷火茂密的横街
年,有人预言:新千年是灾难的源头
并不可信。十三年过去了,当年的
绿洲,也装进了先来者的水囊
明天会有一条新路叠在这条路上
但是今夜,乌鸦还在啄食群星
读诗的人弃笔长眠
雾中的工业时代
工业时代,上帝把教堂收进雾里
屋子很矮,樱桃树和玫瑰园也在雾里
亲爱的,这个消息并不确凿
宣谕的信使骑着机器
轮廓不甚清晰
异域梅花
我住在家乡的房子里
梅花开在酋长的土地上
那时候,大地温暖如炉
梅花最初开了几枝
长满倒刺的香气,就像当年
崔莺莺
坐在香闺中
三月寄别
三月的一天,我送别一个人最后的影子
离电脑不远的地方,水
像时间一样蓝
树林朝一个方向鞠躬,白鹭
刚离开不久
有人在远处竖起耳朵,像
餐桌上的犹大,在这起伏跌宕的世间
喜怒、别愁,都退回体内,收起锋芒
苍蝇的幸福是吮吸一滴糖水
集体的成年尚需时间,不如让这个世界先睡?
三月的一天,一个人最初的影子
终于消失,那是唯一的,沉在波涛里的
船舵。神说:要有光
事就成了,大地分开在脚下,水在树林间
穿梭
每个人都是一座城
那时我在雨里,遭遇一个女人
遭遇一把红伞,一朵半开的花
她在城市的入口,向我问路
一点点暗下是傍晚的光线
我没有请她进来,多少年了
齿轮在风里生锈变冷
一座城市在黄昏点起灯火
树林在身边越长越高
逃离(组诗)
●从明天开始
从明天开始,门牌更换,地址漂移
户口本在柜子里幽怨
邮差和电话找不到你
人衔枚,马摘铃
你在静谧处,生火,造饭
●纸上的大草原
画一些草,一个低矮的山丘
画一些羊低头吃草
画一团云
再画一个面目不详的自己
●在草原上策马
一匹黑色的马,窃来新鲜的夜色
你抱紧马脖,在颠簸中闭上眼睛
夜色已黑,你痛苦地说服自己
胯下的不是长凳,迎面扑来的
不是沉默的墙
●你和一只鸟
你只与它对视一眼
就感觉到拥挤
●膝疼
天转凉了,开始下雨
南昌、上饶、宜春的兄弟
都在淋雨
深圳只有一人
你读到苏轼在岭南醉卧
风湿痛从膝盖里钻出来
●一辈子是多么漫长
一辈子是多么漫长
下午五点五十分,太阳落下
你和一株桂花树,坐在公园里
草莽覆在额头上
●雨落在高处
老乞丐、胡琴、放学的小孩
“你吃——”递到眼前的红苹果
身体还没泊好,在马路边
灯暂时点起,锚暂时抛下
你擦洗云南来的银器
雨落在高处
大批人在伞下偷渡
告诉我,你把他们甩在多前面?
哑城记
一个人的监狱,始于向着王座敬礼
——阿多尼斯
1、
在哑城,只有少数人拥有嘴巴。更少的人拥有声音。一个人开口时,全城人都在记录,声音在耳道里反复死去。
公元前的传统被遵循至今,大部分人拥有吃草的牙齿,极少数人拥有不朽的舌头。
他们自称素食主义者,但他们从不吃草。
、
在哑城,发声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犯罪。只有舌头蜕化得最干净的人才能合法说话。
他们把嘴巴的功效分离开来,只保留进食的本能。
他们是几千年前的幽灵,依旧徘徊不去,在哑城挑选继承者。
3、
不能说话的人,五官都在蜕化:
他们的瞳仁不翼而飞,只能看见眼里的白色。整天,他们以眼白对视,并习以为常。
他们的耳朵遵纪守法,端正地聆听合法的声音——那些软绵绵但形容威武的声音。
他们的嗅觉有了新的功能,分不清兰花之香与鲍鱼之肆,却能嗅出风吹来的方向。
他们的舌头,兴奋地散播口水,用以骗飨各自的缺钙。
他们嫉恨发声者,是因为自己不是那个合法发声的人。
4、
父辈是哑巴,祖辈也是哑巴。他们哑得很虔诚,充满技巧——不虔诚的人都死了,名字都遮盖起来。
不发声是一种荣耀,金子与竹简,谁更诱人?
当有人握住地下的刻刀,在哑城恬不知耻地裸奔。他们就要付出代价,为他们不曾穿衣的肢体语言。
不,肢体语言也是被禁止的。“法律一视同仁!”精神上的哑也必须贯彻到肢体里去。
所有的神都要被消灭!
醉着痛哭的人,要警惕自己的呜咽,不能越过雷池一步。
5、
我降生时,向父辈问路。
他在无处不在的灰白墙壁上写:
哑城没有路。
6、
哑城只有一种颜色
哑城只有一种气味
哑城只有一种声音
哑城只有一条路
7、
在哑城,我看到了他们的墓碑,那在一次又一次暴动中倒下的名字。他们被墨渍涂污,不可辨认。生前的寒意,也带进墓穴之中。
他们的名字:胡风、陆兰秀、林昭、张志新、遇罗克……
8、
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墓碑。当那个我向之问路的父辈带来一整队军警,他说:“就是他”
——这或许可以为他换来说话的快感和荣耀。
在哑城,雄辩属于死去的人,而我不是被挑选者。
9、
有一条衰老的舌头,在火车站吹哨。他的哨声是哑城另一个“合法”的声音。
他曾是前一个发声者的哨子,当他的哨声吹响,挡在前面的人都要向两旁让开。但他的时代已经结束,它成为了一条无用的遗弃的舌头。当他日复一日,在从没有火车停靠的车站吹哨,他的哨声连众人的口水都吓不退。
只有一个三岁的孩子被哨声吓哭——他还没有套上笼口。
人们一边挤出嘲弄的笑容,一边把孩子交给闻讯前来的军警。
10、
我还活着,但如每一个胆敢开口的人一样,我领到了自己的墓碑。
精神上的死亡必须先于肉体!
我看见他们为每一个孩子套上笼口,寒意立刻穿透我的立场。
人们为缄默鼓掌,为唯一合法的声音让出道路。
而道路是大地无法平复的创口
(我看见套上笼口的孩子们坐得笔直,但有一个孩子却在写诗)
什么是诗歌?诗歌是不可言说之物。
在哑城,诗人就是最伟大的罪名。
城市历险记
散会后我不得不中断我的探险
主席英明,赐宴东湖会所
垂头丧气的建筑群跪拜接旨
铁青的东湖,畏光的地下停车场里
饥饿的战场在呼叫老兵。是抽烟的好机会
某种得道的征兆在前排上演。
我想起我那同样脸色的穷亲戚
在狼藉的玻璃柜台前嚎啕,哀悼
夜半失窃的那半条香烟。当我
沿着信江抵达风暴的中心
暴跳如雷的副局长正与“副”字结怨
黄主任在酒桌上频频逼宫
李秘书红着脸继续高歌猛进
江面上的灰鹭再飞低点就进了砂锅
技巧已经失效,酒桌的战场上
中枪的人哈哈大笑,空瓶随风倒戈
回来的路上,我在一棵树下
浪费了纳税人的子弹
四中的女同学掩鼻而过,我看见你发亮的头发
像来自北宋末年的夜色。我在观察你
黑色发卡、海魂衫、短裙,年轻而干净的
身体。一匹漂亮的,未成年的小牝马
现在你还能在沼泽边上,跳着舞
那个长着青春痘的护花使者,目光也在倾斜
在唯一的中心广场,我又看到一条丑陋干皱的
老蜥蜴,拖着沉重的小吃三轮车,走在晦暗的丛林
像一个脸色惨白的老人,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真的,我看见一条黑狗仗着人势对他咆哮,好像
想将他吞下腹中。我看见机动车溅了他一身泥泞
像一头暴躁失眠的犀牛。我担心他老火锅里涮着的肉串
是否像爪子里的纸钞一样猥琐,可谁能抓住他
而不弄断它干枯的尾巴?
我回到临时的巢穴,用浓茶水清洗我的胃
用六万首诗擦拭眼睛,均告失败。
我抱着干燥的床板睡了一夜
又一夜,胃痛折磨着我,孤独苦闷不满愤怒失衡
那些无法言说的钝刀子,在细细凌迟
看不见的痛苦就在那里
在9月3日的黄昏,我将继续尚未完成的探索
继续寻找地砖上烤熟的蚂蚁,散落在禁地里的骨骸
我想找到昨天那条神秘的路线,但指南针业已噤声
我想我那脸色铁青的穷亲戚,但她两年前已死于癌症
======================================================================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