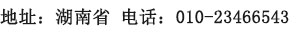在此分享一篇原创文章。
感谢石室届学姐轻山友情供稿。
“此册无题、无名,只有我们,五陵少年仍嫌年少,我们此时,已是最好的模样了。
”作者|轻山
“咯吱——”阁楼的木门被银发的老人推开了一道缝。
“嗒”、“嗒”、“嗒”,脚步声在狭窄的空间中显得格外悠长。阁楼的窗户正对小城城郊的教堂钟楼,彩绘的圣母像每天都隔着遥远的思念慈爱地看着老人。小城是还未被规划的原始模样,低矮的平房,尖顶的洋楼,错落不齐,葱葱郁郁的梧桐生长在建筑群里,优雅自持,像维多利亚时期戴着礼帽的绅士。老人在灰尘中咳嗽着,即使是每天清理,阁楼中总有散不去的霉味,而灰尘,永远会在老人走后从角落滋生出来。阳光温暖,宛如一句耳语,老人想到了什么,他悄悄加快了步伐。其实这时的小城还没有苏醒,斑斓的光影将阁楼的木板地分割成明明暗暗的很多个世界,老人从楼下一路上来,影子在他的衬衫上跳动,就好像,五十年前的夜晚。
阁楼上空空荡荡,只有一把瘸了腿的雕花椅子和磨破了角的长方形桌子。老人走到桌子前面,扶着布满划痕的桌面站了一会儿,稍稍喘了一口气。老人世家是木匠,这张桌子上从原料到成形的木工数不胜数,但是也就到这儿了,他当初一意孤行,远渡重洋,也就断了家里引以为傲的传承,最后这张桌子,也就沦落到在阁楼的阳光里,等待自己腐朽的死亡。老人安安静静地在椅子上坐下,用肿胀、干裂的手指抚摸着失去了包浆的木椅。他浑浊的眼睛中闪过一道光,仿佛是遗憾,也仿佛是怀念。桌子里一个抽屉,抽屉里躺着老人的宝物。
他拉着抽屉上的铜扣,慢慢取出那一件宝物。蓝布皮中包着毛糙的书页,几年前它在外孙的手里散了架,老人就再也没有把它放在书架上了,何况这也是家人不知道的一个秘密。老人微微闭着眼睛,其实书的第一页——那页卷首语,他已经熟记于心了,他怀想着,写下它的那个人,当初的神情如此温柔,虽然她知道自己再也走不出那片呻吟着的土地了。
“诸君安否?幸得此契机,实是感激不尽,恭疏短引,然才疏学浅,只想着捡几句寻常话,道道肺腑罢了。
相识三载,历寒窗、赴远洋,格丽丝嬷嬷临别时赠的那只布袋不知诸君还留存否?一针一线,仿佛得闻学校那丛栀子的芬芳,然而嬷嬷已经远在天国了。主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里除掉你们的恶行。’嬷嬷是义人,她走了,将福祉赐予我们,也是告诫我们,日光之下,必不可生恶。”老人读到此处,用力挤了挤疲惫的眼睛。他想着那个偏爱棉布旗袍的女子,五十年前也是执着一本《圣经》推开了学生公会的大门,自从他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就再也没法从那双深色的饱含着悲悯的清澈眼睛中逃出来。
“此地罹难,恨吾力不足,无以救济,祸兮祸兮,前日布莱恩家长子离世,相伴三旬,感情实笃。世事无常,近日常忆起他的种种善举,疫区清洁,皆由他一手包办,我等之不及,岂以分毫相量。今早起床略感不适,我已心知肚明,将死之人,其言也善,就放纵我固执这一回吧,此序不成体统,胡言乱语,望诸君海涵,当成一封家书,也就不讲究了。”
“梁君、方君,第三个安息日便已不见他们,不知安然回国或是仍在外风雨飘零?人生而畏惧死亡,我无意责怪,只是音信全无,难让人放心,烦请诸君将纪念册备下一份,如若往后得以遇见,也算补全我的一个心愿。
郑君、齐君,家中尚有老小,于我更是温厚慈爱,愿他们早日归国。济世、齐家,皆是责任,家中老母念念、幼子嗷嗷,便已不宜留在此地,若两君执意不去,是妹妹我恳请了,见着你我三年的情分上,回家吧。”
老人想着,她面对着空空荡荡,只散落着几张废纸的居室,脸庞隐藏在窗棂映下的阴影里。他们不告而别,甚至没有一个愧疚的眼神留给仍在遗弃地工作的人,就这样悄悄地离开,如同早晨睁开眼忘记一个梦一样简单。她不发一言,只是那个背影,已然成了一句悲伤的叹息。她默默走向窗户,打开活栓,推开那两扇紧闭的玻璃,阳光宣泄下来,点亮她的一头黑发。停留在窗台上的鸽子受惊腾起,她牢牢抓住窗棂的双手,在颤抖中透露出她的情绪。他翕动着唇,干涩的喉咙吐露不出宽慰的话语。他想告诉她,其实他很早就看见他们将随身的物品置换成钱财,他想告诉她,他们几次深夜未归是为了联络码头,他想告诉她,或许偷渡船的船工接受了他们的“好意”,他们已经开始打包行李,他想告诉她,她为他们这几天的尽心尽力而感动,其实那不过是对自己过错的一种弥补,她没有看见他们的警惕和讨好。他知道,或许她也知道吧,但是没有用的,你无法去苛责一个为了活下来而放弃一切的人的人,更何况他们是你的朋友。但是他想告诉她,他会陪她走到最后,他也会在她之后离去,他不想让她看见多一个人的死亡。
但是啊,这些都没说出口,这些应被知道的,应被审判的,应被原谅的,都没有公之于众,他们留下来的人选择了缄默和承认,在心底默默计算着自己的极限。他终究没有履行诺言。
世事无常。
“余常记起,来这边的第一个舞会。那是我等最团聚的日子,方君、梁君,去弗娜街上置办西服,珍小姐带着我们在一旁歇息。诸位还记得那日的柠檬汽水吗?方君换上西服不肯脱,合着我咬着吸管啜着汽水,谁料柠檬籽堵了管口,他都一口水呛住了,那套西服算是糟蹋了,他强装镇定掩不住心疼的样子,实在可爱啊。苦了我和珍小姐笑抖了肩,还要帮他擦拭襟上的水渍。晚会上和他共舞的女子对珍小姐说:‘Hesmellslikealemon!’珍小姐笑得直不起腰,回话道:‘Heisnotalemon!*’那时真快活啊!”
老人轻轻弯了弯嘴角。他想着她第一次参加舞会,就像春天里开出的第一朵花,在悠长的乐声中带着点青涩地绽放,淡蓝色的裙摆在空中划过一道道水纹般的弧线,仿佛唤来了珀耳塞福涅,大厅里满是玫瑰的馥郁。她微微喘着气向穿着父亲的旧西装,处处蹩足的他伸出双手,就仿佛向他形单影只的冰冷世界投来了一束光,她嘴角噙着笑:“——”
外面的天色愈加明亮。阳光慢慢攀爬到窗棂最高处,有一缕直射进阁楼,缠绕在老人身上,令他不得不打断了自己的回忆。老人眯了眯眼,用手掌挡住干净纯粹的光亮。
“自今日,吾命已不久,至此不提秉承遗志之言,只望诸君行其所向,无愧于心而已。然遇讎者容之,遇穷者怜之,遇不合者尊之,遇高尚者敬之,遇愚者启之,遇智者询之,遇投契者同归,虽人力无以改生死,亦不枉此生了。我与诸君相识相知,此番去前,想求得知己一称。‘高山流水’是难再了;遥隔数里,温酒话桑麻怕也做不到了,但你我心意相通,也无需风儿、明月捎话,我的言语已尽,种种情绪不必再提。”
“您愿意共舞一曲吗?”老人想到了她当时所说的话语。冰雪聪明、心细如发,人人皆说她善良。他含着羞怯对她说出“谢谢”,她只是笑了笑。他想搭话,也结结巴巴地夸了她善良,她的笑渐渐淡下去,有一丝苦涩。他自觉说错了话,慌张说着“失陪”逃向了舞池边缘。
后来的后来他知道了原因。她却说她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她街上给无家可归的乞丐送去一碗热汤、去陪伴残了手脚的儿童、去照看躺在病床上没有儿女的老人、去匿名资助吃不起饭的学生,虽是源于不忍,但实则是期望通过拯救他们,洗脱自己生而带来的罪名。她将自己的内心剖开来,强硬地、执着地摊开在他的面前。她说,她能给予的无非是痛苦中一点温暖的假象、她能安慰的无非是忘记了如何去希望心灵,她所能够救出的无非是无辜灵魂的肉体,但是,言语、拥抱、药品到现在都没了用。
“执笔写下这几个字,我已是疲惫不堪,病痛时常在深夜叨扰。或许大限已至,过去遗憾的、悔恨的在夜深人静时纠缠着我,我看见那些人们手上溃烂的伤口、红紫的在疼痛中逝去的面庞,这是一个邀约,我辜负了他们,我们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使最后的绝望更难以接受,他们宁愿死后收到刑罚也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何等可恨,但我不能放弃,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包括我自己,我都要与疫病抗争。神降难于人类,虱灾、蝗灾,是因为人类拒绝侍奉神明,将神的圣徒赶出门外,我愿意用生命来洗清罪罚,请惩罚我吧,人何等无辜,何等无助!”
是了,她奇异的虔诚。“我生而是罪人。”仿佛有人在老人耳边喃喃。他想起她谈及自己的家庭时,那种平静下的沉痛,隐藏到深处好像近乎麻木。老人背靠在椅子上种种喘了口气,风箱似的肺在宣示着老人无多时日。“我知道,我知道,就像她那样。”老人默默对自己说。他闭着眼努力回忆起她的身世,那的确是一段不太愉快的经历。“医院,我的母亲是修女,而父亲,是战后遗族。父亲为保护母亲和我被打死了,母亲肺炎未愈缠绵病榻。母亲待我极好的,父亲待我,也是极好的,我喜欢他们一起抱着我在暖阳下哼歌,儿歌、圣歌、还有山民的曲子,虽然我连父亲的脸都记不住,但是我明白了,什么感觉叫做家。”母亲,母亲叫我待仇人如待爱人,她犯了错,说谎、不贞,所以要承受苦难。她在临终前的那一个月,执意拖着残躯,扶着楼梯,独自下楼透风,她上来的时候,带了一只折了腿的猫崽,她将它断腿处的杂毛剪掉,简单做了一个支架,把它抱在怀中,教导我如何去安抚战战兢兢轻轻抽搐的猫崽。两个人,一只猫,母亲为猫梳理着毛发,我打点着家务。最后,她把它送给我,”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候的感受,母亲用她的眼睛看着我,猫崽试探着舔舐我的手心,母亲抬起手揉了揉我的发顶,又拍了拍。她的眸中有微笑,她在说:‘我的女儿都长那么高啦,我很开心。’她在说:‘你是大人了,妈妈很放心。’她在说:‘对不起,妈妈要走了’我在那一刻仿佛接到了神启,柔软到极致的、温和的、把我包裹的母爱,是神告诉我的,唯一能够解救我的家庭的东西。是母亲划破血肉最后留给我的东西。”
“——母性,来自母亲的爱,来自神的宽恕的爱。”
“母亲说:‘我不能去天国了’,她说她去找我父亲了,她会为我祈祷的,神明会护佑我。”“我的出生不被期待,但我曾经拥有过他们,已是神给我最大的赐福。我想告诉其他人,他们很好很好,他们只是父亲、只是母亲。我要替他们背负十字架,我要去救助更多人,这是他们期望我做的,也是能够在他们死后我为永受罪愆的他们能够做的”“我原来想救千千万人,想救被疾病折磨的人,想救这个小镇上的人,想救周围的人,想救我熟识的人,想救我的朋友们,现在,只想就一个人就好……”“我现在,只盼着能救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就好啊……”
老人猛地睁开眼睛,剧烈的咳嗽起来。他费力转过头,用手绢捂住嘴,雪白的方块上开出朵朵梅花。“你呀……”老人抑制住胸口中翻腾的痛苦,他说不出一个字来。
“昔日光彩的大街已经成了废墟,我已记不清当年我们从书社出来一路高歌到凯瑟酒馆的模样了,只记得不在乎他人的眼光,一路放歌的恣意。我们谈论释、儒、道,郑君说空门不如出世,方君说出世不如入世。梁君说他们大话空空,不如身体力行,我当时只顾着笑,倒是没有多少高见。”
老人放松了身体,脆弱的骨骼在凳子上轻微的晃动着。“子钰!子钰!毛巾和热水拿到三号房!”老人耳中响起了女子焦急而清晰的声音。“阿姆,阿姆!你再等等!科里马上来了!阿姆——”她有多少次哆嗦着握住逐渐冰冷的手,也有多少次直视死亡的丑恶,她的眼中总是噙着泪水,即使是最后的那个时刻,她的眼睛好像在道歉,对每一个人,对整个世界。
老人放任自己陷入无边的回想。
“我与诸位同庚,诸位是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亲人,诸位的品格熠熠生辉。赵君,已故有月余,我不想落泪,但实在无能为力,我悔惜他一身的才华,我景仰他磊落的品格,’高山仰止‘,于赵兄再合乎不过了。界外的人避我们如蛇蝎,他虽然只做联络工作,带着一身的伤回来,已经被我撞见数次了。他毫不在意,他不去怨恨、不去感叹世态炎凉,只是为生病的人掖好被子,为送来的人登记安排歇息的地方,为每一位远去的朋友刻下墓碑,再静静地看着他们火化。他是我的引路人,我实在是无法控制地想念他,愿他在天堂一切安好,神是公正的,害他的人群必不会好过。”
“我要向神忏悔,神说不可生害人之心,我却为了自己的情感诅咒过伤我之人,为了给人虚伪的安慰而欺瞒撒谎,为了让自己走得平静将更大的痛苦留给你们,神啊,我要忏悔,我不祈求宽恕,不祈求免罪,我祈求留在这世上之人安稳健康,再也不要有这样鼠疫滋生的灰暗之地,不要有像我们这样的人。”
“远宁,咳、咳,这个你交给弗朗士,阿公知道他期盼这套邮票好久了,你交给他,给他说带着阿公的份攒下去。”素白的手伸过警戒的栅栏。
“啊!有面包?你们自己做的?真不错啊,好香……给我的?好呀,我得拿回去分给孩子们,他们想你们得紧呀。”
“咳、咳……咳咳。你,你们下周不要来了,这天气变化着实大,这不,我又被流感找上了。你们别离我太近。”
“多日未见,看你们怎么又瘦了?”“咳、咳咳”“国内有消息了?几时的船?17日?好的,好的……”“呼、呼”“我是送不成你们了,回国后,烧几张东篱先生的书给我吧,这几年没时间读,现在得空了。”
“咳,快走吧。”
“姐姐她,她起不了床了……你们……她让我告诉你们,早日回去,心送君千里。”
老人回想起男孩蹩足的中文,忍不住滚下浑浊的泪水,黄褐色的苍老面庞上爬满了透明的水渍。她崩坏了指甲的指尖是如何抠着病床床单才不至于发出呻吟;她烧的通红的脸庞是如何在昏迷和清醒中挣扎,惦念着远方的朋友;她在流感和疫症的折磨下如何攥住十字架一字一句地祷告,戳破手掌的鲜血如何浸湿了她衣襟滴落在病床上……老人无从知晓,只知道自己发疯地跳下船往回赶,被众人拼命拦下,他无法想象,她是如何孤独地坐在病房里做最后的祷告,如何忧伤地哼唱着小时候听过千百次的摇篮曲;他无法透过濛濛泪眼,看见一个没了生气的人,蜷曲在瓷砖地上,眼睛没有合上,神态却似有安详。
他在归国的那段日子里夜夜浅眠不时被惊醒,他听得到他们的呼唤,和蔼的人们仿佛还围着他,递来一条核桃面包、一瓶草莓酱、一罐蜂蜜,他披着外套走到甲板上,镜子般的月亮高高悬挂在海面上,他想回应那些话语,想同他们一起走,但是恍然间他在月亮里看见了她的眼睛,温柔的、真挚的,洗清世间不愿在夜里隐藏的污浊,那一刻,远洋的船漂泊,游子却回到了故乡。
“再说下去,也并无益处,只是胡诌几句文言,嚼嚼自己多苦多累罢了。本无意给诸君添堵,我打算就此结束,先恕我难以同你们走下去,别过了。”
“我会带着它安眠于地下,假以时日,我的坟上长出青草,有鸟雀停驻,便是神承认我这个儿女了。我负罪活了小半辈子,没有后悔停留在这里。我去见父亲、母亲,诸后事宜,劳君费心。”
“此册无题、无名,只有我们,五陵少年仍嫌年少,我们此时,已是最好的模样了。”
“祈安康。”
医院的门口,雨露凝集在柔弱而圣洁的花瓣上。
洁白的、尘世的玫瑰啊……你的灵魂,是否也已远去?
你小时听的那段摇篮曲,还在被人传颂……
母亲唱啊:你乖乖睡去,梦中无惊无扰,只有羔羊与橄榄叶;
你此生没有苦痛,行在峡谷,会遇见你的牧者;
他也是洁白的打扮啊,手上拿着他的杖;
他领你同去,同去,去那光耀的世界;
你不要害怕呀,快去快去……
睡吧孩子,睡吧;
妈妈陪着你,睡吧孩子……
梦中只有甜蜜,你是我的花儿呀,是圣母玛利亚的赐福;
你是我的光呀,是约书亚;
你快睡吧,睡吧,妈妈陪着你……
老人缓缓放下手中的书页,站了起来,木椅脚划过地板发出悲伤的长叹。远远地,教堂钟楼上的指针已经要指向整点,老人等待着那一刻。
“咚、咚——”老人感觉时间仿佛变快了,阳光加速漫进阁楼,蔷薇、鸢尾的芬芳随着云雀的啼鸣婉转、袅绕。
“咚——咚、咚——”老人独自走进未被抹去的阴影,木板再次发出“嘎吱”的声音。他好像听见家人的呼唤,稍稍加快了步伐。
“咚——”铜制大钟最后一声严肃辽远的钟声,彻底唤醒了小城。教堂大理石穹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明媚、带着一点温柔,钟楼再次恢复了沉静,如过去的百年般,疏离地品味着小城里的人情世事,悲悯地看着那些凝望着它的人。
阁楼上没有了任何声音,骤然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金黄的灰尘,开始自己短暂的一生。
*lemon:俚语,讨厌的人。
后话︱作者的灵光一现
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行香子·述怀》苏轼
文案/轻山
图片来源/LOFTERID:licheng
排版/Arno
拾潮
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