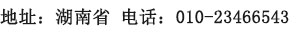量子与纳米科技极度发达的未来,记忆可以制造,人格与意识被无限复制,永生不再是梦想。
假如死亡只是暂时的,生命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我能抹去自己的记忆,我还是我吗?
太阳系最厉害的“绅士怪盗”赌王若昂越狱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偷回自己的记忆。他将在真是与虚幻间游走,与太阳系内的不同势力斗智斗勇,不但女找自己的过去,也抽丝剥茧,揭开未来的真相。
量子窃贼
哈努·拉贾涅米著胡纾译郭建图
“……如果你不断装扮成这个人、那个人,总会有那么一刻,你不再认识你自己了。这真是太可悲了。此刻我的感受,大概就像失去了自己影子的人一样……”
——莫里斯·勒布朗,《罗萍大冒险》第三章,《亚森·罗萍逃脱》
1
窃贼与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两名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为什么即使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具体如下: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五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凿,两人都判刑两年。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在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囚徒困境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表明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跟战脑互射之前,我照例想先聊两句。
“哪儿的监狱都一个样儿,你说呢?”
其实我连它听不听得到声音都不清楚。它没有可见的听觉器官,只有眼睛,人眼,总共好几百。眼柄从身体各处向外生长,眼睛长在眼柄尽头,活像热带水果。我俩的牢房之间是一条闪亮的界线,它飘浮在线的另一侧,偌大的银色柯尔特手枪握在小树枝一样的机械手里。可这副怪模样我却笑不出来,因为我已经被它射杀了一万四千回。
“监狱活像过去地球上的机场。谁也不乐意来,也没人当真住在这儿。我们都只是过客。”
今天,监狱的墙是玻璃。头顶上方老远挂了一轮太阳,跟真货差不太多,但又有点不大对劲,更黯淡些。在我周围,数百万间牢房延伸至无穷远处,一色的玻璃墙壁、玻璃地板。光线渗过透明的表面,在地板上造出彩虹的颜色。除了这些颜色,我的牢房光溜溜的,我自己也一样,新生儿似的不着寸缕,只手里握着枪。有时候,如果你赢了,它们会允许你做一点小小的改动。战脑最近成绩斐然。它牢房里飘着零重力的花,红色、紫色、绿色的球茎从水泡里长出来,活像卡通版的它自己。自恋的混蛋。
“如果牢房带厕所,门肯定朝里开。永远一成不变。”
好吧,我真的快找不出词儿了。
战脑缓缓举起武器,眼柄上仿佛荡开了波纹。它要是有张脸该多好,那么一大片湿乎乎的眼球盯着你,真叫人心慌。别管那个了,这次一定能成功。我稍微把枪抬高,肢体语言和手腕的动作都在向对方诉说我的意图,我的每块肌肉都在高喊“合作”两个字。来吧,相信我。不骗你,这回咱们做朋友——
火光闪过——它黑洞洞的枪口眨了眨眼。我扣扳机的手指跟着一抽。两声霹雳似的枪响之后,我脑袋里多了粒子弹。
滚烫的金属钻进颅骨,再从后脑勺蹿出去——这种感觉你永远不可能完全习惯。模拟的细节详尽逼真,让人叹为观止:热流穿透前额,温热的血水和脑浆喷洒在肩膀和后背上,接着是突如其来的寒意——以及最后的黑暗。一切陷入停顿。“困境监狱”的牢头阿尔肯族就是要你好好感受。这是为了教育你。
监狱的一切都是为了教育。还有博弈理论:关于理性决策的数学。阿尔肯族是长生不死的精神体,自然有大把工夫可以花在这类破事儿上。而内太阳系的统治者、上载的集合体索伯诺斯特,偏偏指定它们来管理监狱。
这个游戏的原型一直是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宠儿。同样的游戏我们玩了一次又一次,形式时有不同。有时它们让我们玩比试胆量:驾车相对行驶,飞驰在没有尽头的高速路上,决定要不要在最后一刻避让。有时我们是困在战壕里的战士,隔着无人区遥遥相望。有时它们回归传统,把我们变成囚犯——老式的囚犯,被神色严厉的家伙拷问;我们必须在背叛同伴和遵守缄默法则之间做出选择。今天的趣味是枪。我对明天毫无期待。
我像皮筋回弹一样“啪”的活转来。我眨巴眨巴眼睛,感到脑子里有一处不连贯的地方,一点粗糙的边缘。每次还魂,阿尔肯都会稍微改变你的神经构造。按它们的理论,达尔文的磨刀石终究会让所有囚犯改过自新,变成合作者。
如果对方开枪,我没开枪,我就完蛋了。如果我们都开枪,双方都会有点痛。如果我们合作,双方都能中大奖。只不过总有些东西会诱惑你扣动扳机。但阿尔肯认定了一件事:只要我们不断相遇,合作行为终会出现。
再来几百万回合,我准能变成童子军。
才怪。
上一场对决之后,我的分数实在要命。我和战脑都背叛了。这一轮还剩两场。不够啊,见鬼。
跟邻居对战,赢了可以获得领地。每轮过后,如果你的分数比对方高,你就赢了。获胜的奖励是你自己的复制品,你可以用它们取代——就是消灭——你周围的失败者。我今天的表现不怎么样,到现在已经两次双向背叛,两次都是跟战脑。如果不能扭转这一轮,我就真要烟消云散了。
我暗暗掂量自己的选择。我周围的牢房,有两间已经住进了战脑的拷贝——左手边那间和背后那间。右手边的牢房里是个女人。我转身面对那间牢房,我们之间的墙消失了,被代表你死我活的蓝线取代。
她的牢房跟我的一样素净。她坐在地板中央,双臂抱膝,身上裹着古罗马长袍似的黑色衣裳。这人过去从没见过,我好奇地打量她:她晒得很黑,让我联想到奥尔特星云人,一张亚洲杏脸,身体结实有力。我微笑着朝她挥手,她毫不理会。监狱似乎认定我的举动已经构成相互合作:我感到自己的分数略微上升,仿佛吞下一小杯威士忌,暖洋洋的。我们之间的玻璃墙回归原位。哇,真轻松。但想赢战脑还不够。
“嘿,窝囊废。”有人开口了,“人家没兴趣。比你强的货色多的是。”
剩下那间牢房里是另一个我。他懒洋洋地躺在泳池旁的沙滩椅上,穿件白色网球衫,太阳镜太大,跟脸型不怎么搭调。他腿上有本书,是法文版的《水晶瓶塞》[《亚森·罗萍探案集》的第六本。]。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它又把你干了。”那家伙连头都懒得抬,“又一次。这是第几回了?连着三次?你怎么还没明白,它的策略永远都是以牙还牙。”
“刚刚我差点就蒙过它了。”
“伪造合作的记忆嘛,点子是不错。”他说,“只不过,你知道,永远行不通。战脑是非标准枕叶和无序型背侧通路,视幻觉别想糊弄它。真可惜,阿尔肯从来不给失败者发鼓励奖。”
我眨眨眼。
“等等。这些事儿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你以为自己是这鬼地方唯一的赌王?还有我呢。不扯这些了,你还差十分才能赢它,赶紧过来,我帮你。”
“你就尽管挖苦我吧,机灵鬼。”我朝蓝线走去。自这轮开始,我的呼吸头一次轻松起来。他也站起身,从书底下拿出线条流畅的自动手枪。
我伸出食指对准他。“砰砰。”我说,“我合作。”
“真够逗的。”他边说边举枪,还咧嘴冲我笑。
他的太阳镜里映出两个我,两个赤身裸体、毫无遮掩的小人。
“嘿,嘿,咱们是一伙的,不是吗?”亏我还自以为挺有幽默感呢,比他差远了。
“投机客、大冒险家,咱们不就是这种人吗?”
我心头一动:真诚的微笑、精致的牢房,让我放松、让我想起自己,但又总有些地方不大对劲——
“哦见鬼。”
牢里总少不了各种传闻和鬼故事,这儿也一样。我曾跟一个变节的佐酷人合作过一段时间,这故事就是那人告诉我的:畸变体的传说,终极背叛者,绝对不合作而又能一直逃脱惩罚的东西。它找到了系统里的一个漏洞,因此永远以你的形象出现。如果你连自己都信不过,你还能相信谁呢?
“哦没错。”终极背叛者扣动了扳机。
总算不是战脑,我一面胡思乱想,一面看着眼前闪过明亮的霹雳。
然后一切都变得莫名其妙了。
梦中,米耶里正在金星上吃桃子。果肉甜美多汁,微微发酸。与席丹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十分可口。
她重重喘气:“你混蛋。”
克里奥佩特拉陨坑上方十四公里处,一个Q粒子泡泡构成了人类的小巢,让她们得以在马克斯韦尔山陡峭的断壁上流汗、做爱。硫酸风在外面咆哮。云层琥珀色的光线穿透坚硬无比的人造物质外壳,把席丹的皮肤染成紫铜色。她的手掌放在米耶里依然濡湿的性器上方,与阴阜的轮廓正好契合。米耶里肚里仿佛有无数翅膀,正懒洋洋地轻轻扇动。
“我做什么了?”
“做了好多。人家在固伯尼亚教你的就是这个?”
席丹露出古灵精怪的微笑,眼角尽是细密的鱼尾纹。她说:“实话告诉你,我好一阵子没做,有点生疏了。”
“屁。”
“你的屁股很棒呀。”
席丹伸出空闲的那只手,手指抚上米耶里胸部的蝴蝶纹身,描绘它银色的线条。
米耶里说:“别。”她突然觉得很冷。
席丹缩回手,碰碰米耶里的面颊。
“怎么了?”
果肉吃尽,只剩果核。她把它含在嘴里,过了片刻才吐出来。坚硬的小东西,表面刻满记忆。
“你并不是真的跟我在一起。你并不真实。你在这儿只是为了让我别发疯,在监狱里。”
“有效果吗?”
米耶里把她拉近,吻她的脖子,嘴里尝到汗水的味道。“没用。我不想离开,所以准是疯了。”
“你从来都比我坚强。”席丹轻抚米耶里的头发,“时间快到了。”
米耶里抓紧她,抓紧对方身体熟悉的触感。席丹腿上宝石镶嵌的蛇紧紧压着她。
米耶里。佩莱格莉妮的声音传入她脑中,仿佛一股冷风。
“再一小会儿——”
米耶里!
转变来得又猛又痛,就像一口咬在桃核上。现实的果核坚硬无比,几乎崩断她的牙。牢房、苍白的人造阳光。玻璃墙,墙背后是两个贼,正在交谈。
任务。好几个月,漫长的准备与实施。转瞬间她便完全清醒,计划在她脑中展开。
不该给你那段记忆,她脑中的佩莱格莉妮说道。险些误事。现在让我出去:这里越来越挤了。
米耶里朝玻璃墙吐出桃核。墙壁像冰一样碎了。
9月《科幻世界·译文版》已上架
赞赏